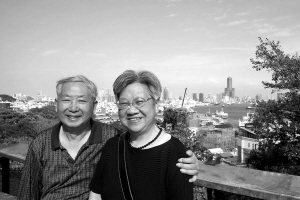 |
| 王重光与妻子陈爱娣 |
他的作品 《中国帝陵》 在文史爱好者中引起不小轰动 王重光先生生前曾经说过,自己的墓志铭上只要写一句话:“《中国帝陵》的作者:王重光和陈爱娣”。 陈爱娣是王重光的妻子。因为两家的父亲同在上海的四明大药房里做账房先生,两人在一个大院里出生,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后来相继辗转回到宁波定居,一个性格刚强,一个温柔贤淑,相濡以沫了一辈子。 “1991年初,奶奶去世了。我父亲和奶奶同一天生日,他们的感情非常深,却没能赶上见奶奶最后一面,他非常悲痛。后来我母亲为了安慰他,就鼓励他说,虽然奶奶是一个不识字的母亲,但可以培养出一个写书的儿子。”王重光的女儿王国瑾昨天回忆说,正是因为母亲的这句话,学理工科出身、当时年过半百的王重光凭借兴趣,独自踏上了漫长的帝陵探访之路。 因为工作关系,王重光曾去过中国很多地方,到过北京定陵、清东陵、秦汉唐古墓陵。为了亲近历史遗痕,他带着相机一路行山踏水,拍摄了几百张照片,多次与死亡擦身而过。最危险的一次是在山西临汾考察尧帝陵时,行走在杂草丛生荒冢里,王重光跌落人迹罕至的深谷,醒来后自己爬出了深谷继续考察研究。 王国瑾说:“《中国帝陵》的书稿有几公斤重,三十多万字。书中的很多地图和图表都是父亲自己画的。1994年,父亲背着半麻袋的稿纸,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毛遂自荐。主编一看书稿,大为震惊,很快决定出版,书名为《中国帝陵》。”1996年,《中国帝陵》在上海和台湾相继问世,在文史爱好者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走遍宁波》 成为宁波旅游界人士必读之书 王重光“自费考古”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宁波大学邀请王重光去演讲,讲述他的人生经历和创作《中国帝陵》的故事,王重光说:“我是那种‘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宁波人,从心底里爱家乡,我以宁波人看故乡,以浪迹天涯、四海为家的游子之心看故乡。以一个普通的旅游者看故乡,看她的风流七千年,看她的四明八百里。” 从1995年开始,王重光与甬上书友策划文化旅游,以“亲近家乡山和水,感受故土今与昔”为口号,边走边看边议论,用抒情散文的形式记录。2001年,王重光的《走遍宁波》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一万册新书一上市即告罄。该书一版再版,是宁波旅游界人士的必读之书,也成为新宁波人了解这座城市的入门书籍。2002年,《走遍宁波》获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 为弘扬家乡的历史文化,王重光的这种挚爱有时甚至到了常人无法理解的程度,“我父亲性格很固执,自己决定的事情一定要做。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这种固执让他坚持这么多年对宁波历史文化的探寻和保护。”王国瑾说,11月初,父亲还在写关于宁波服装博物馆发展前景的文章,写了两万多字,“服装博物馆的馆长来看他,说等他病好了再请他回去指导工作,父亲也很高兴”。王重光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而他的日记最后停留在了11月19日。 他的执着 多方论证 《三字经》作者是王应麟 在王国瑾的印象里,父亲一直致力于发掘与宁波的历史文化价值相关的东西。 《三字经》是我国古代最为流行和影响最大的蒙学读本,作者世传为宋元之际的鄞县人王应麟。王重光出于对先哲古贤的敬仰和文化经典的珍视,早在1996年就率先发起了“纪念王应麟逝世700周年”的系列活动,得到了甬上文化界和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 2007年初,浙粤两地发生了《三字经》作者的学术之争,有人认为是广东顺德人欧适子,有人认为是鄞州人王应麟,王重光执着地坚持认为是王应麟,并搜集了很多材料,佐证自己的观点。 他还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寻找各种版本的《三字经》,他甚至前往日本寻找《三字经》版本,目前,三百多种《三字经》版本都印在了他的《<三字经>古本集成》一书里。 在整理考证基础上,他还对每种版本加上“编者按”,交代版本来历,介绍作者概况,评述内容特点,以便今后阅读、检索,作为学术讨论之工具书、参考书。 而小提琴大师马友友的寻根之旅也在王重光的再三努力下促成。并非音乐迷的王重光,只是因为马友友的祖籍在鄞州而关注了他整整18年。由他编写的家书《月是故乡明》飞越重洋抵达远在美国的马友友手中,终于让这位游子在2005年踏上回家路。此时的王重光却积劳成疾,躺在了病床上。在马友友离甬后,他又在病床上写出了《马友友琴系故土》一书。 他的贡献 力促保护 咸通塔和张苍水故居 在宁波,很多人知道王重光,除了看过他的书,还因为他几十年如一日,对甬上历史文化孜孜不倦的探寻和保护。前童古镇、徐霞客古道、野鹤湫瀑布、达蓬山历史遗迹、南宋石刻、张苍水故居等历史文化的发掘保护,都倾注着王重光和杨古城、曹厚德、王介堂等人的心血。 在宁波改革开放早期,有两个不可移动文物就地保护的成功案例都与王重光有关。 1995年,王重光受邀写一则关于中山西路拓宽道路北侧一座历史文物咸通塔的去留问题。文化部门坚持要就地保护,因为咸通塔是我国江南地区唯一幸存的唐代方形砖塔。而市政建设部门鉴于道路拓宽后地下管线施工的困难和风险,建议易地迁建该塔。双方争论已达数月。一天,本无发言权的王重光在会场拍案而起,“唐塔不能拆!”虽然这一喊扰乱了会场秩序,但正因这一声,唐塔的命运发生了奇迹般的转折,建设部门提出了新的施工方案,地下管线绕行,唐塔保住了。 1998年,由于中山广场的开建,张苍水故居同样面临易地拆迁的命运。王重光和王介堂等文保志愿者经过实地踏勘之后起草了《就地保护张苍水故居的紧急呼吁书》,再度奔走呼号,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里经历数十个回合,终于出现了转机。 成功保护咸通塔和张苍水故居,对于宁波日后的文物保护、非遗保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呢?王国瑾说:“父亲说过,拯救传统文化,对得起古代祖先和后世子孙,再怎么辛苦都是值得的。” ■朋友悼念 孙乃平(王重光的老朋友,民间文化人士):我与重光兄相知相交,一晃已有十五载。 如今,他那生命之火终于在发出最后的光芒后而熄灭。他的确到了应该休息的时候,长眠就是幸福!他曾经和我说过:生命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暗淡,有辉煌。他应该是属于后一种。 ■记者手记 最后一次见到王重光先生是在一年前,王升大博物馆的开馆仪式上。 那时候的他,已经与病魔抗争了8年多。他的眼睛尽管浑浊了,却依然炯炯有神。 讲到非遗的保护现状,他声如洪钟,掷地有声,眼里更是放出光芒来。 吃饭的时候,他坐在我旁边,有问必答。尽管剥花生的手有些颤抖,但说起历史上的典故,依然思路清晰,头头是道。 菜过五味,他放下筷子,悄声对我说:“我已是将死之人了,文化的事情,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了。不要采访我,我的故事三言两语说不完。” 图片由王重光先生女儿王国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