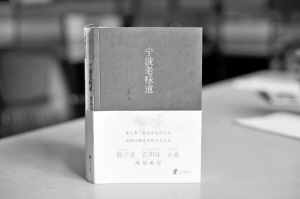 |
| 记者 崔引 摄 |
 |
| 宁式鳝丝浆 |
 |
| 位于南塘老街的余姚黄鱼面馆 |
《宁波老味道》的封面,是扑面而来的春水气息,墨绿色,线装本,烫金字。书脊用白色棉麻包裹,素净安详。 腰封上,是几位名人的推荐:学者陈子善、美食评论家孔明珠、学者止庵。 作者柴隆的名字,隐没在一片苍翠中。低调的他,是个热爱宁波人文历史的年轻人。 斜阳西下的寻常巷陌,浓郁的人间烟火味,还有终日劳碌在煤球炉子前,微驼着背的外婆,就是他笔下的宁波老味道。 七十七道宁波下饭,在柴隆笔下娓娓道来,不由令人唇齿生津。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那何尝不是宁波人精明持家的缩影? 记者 陈也喆 【七浆八浆】 柴隆的宁波话说得很溜,宁波菜也做得很正宗,骨子里流淌的却是山东大汉的血液。 他出生在青岛,9岁随父母到了宁波,读书、工作,做了宁波女婿,早已融入了这座城市。 他似乎生来就喜欢寻味。孩提时代,生个煤球炉,不忘煨个番薯、烘块年糕,偶尔心血来潮,拿铁丝串起肉块,撒点盐,烤成肉串吃。 甬城大大小小的餐馆,几乎没有他未涉足的。遇到心仪的菜,回家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去做,每次都像那么回事。 真正让他对宁波下饭刮目相看,始于第一次拜见岳父岳母。 毛脚女婿刚上门,丈母娘就烧了满满一桌宁波“台面菜”,其中有一碗菜是蒿菜蛳螺浆。 那时正值清明,“清明螺,赛只鹅”,正是螺肉最肥美的季节。蒿菜虽已开花,香气却浓郁,丈母娘把“上市货”与“落市货”搭在一起,味道竟鲜美无比。 他自小在北方长大,看惯了大碗炖肉、大锅煮菜的情景,北方人与南方人的做派,在下饭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后来他悉心琢磨,发现宁波人的桌上总会有些汤汤卤卤,取材多为时令菜。 早春二月,黄鳝刚出洞,韭芽最嫩,黄鳝水氽,划骨取丝,韭芽切段,撒胡椒粉,浇热猪油,宁式鳝丝浆,齿颊留香。 清明前,菜蕻干刚晒好,河里的蛳螺也最肥,一碗万年青蛳螺浆,清火去热。 端午前后,莙荙叶片肥硕,咸菜笋丝鲜美,一碗莙荙笋丝浆,小孩吃了,夏天不生痱子。 夏天到了,夜开花(瓠瓜)上市,夜开花豆瓣浆,清凉爽口。 冬至前后,冬笋新鲜,霜打的天菜芯,消了苦味,天菜芯笋片浆,最是清新爽利。 过年待客,杀鸡宰羊时,又会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杂浆。 七浆八浆,早已深入宁波人的生活。有句宁波老话叫“转浆”,说的就是各种事情凑到一块,忙得不可开交。 老宁波的“七浆八浆”里,蕴藉着江南的精细与风雅。 【做人家】 “做人家”是柴隆反复提到的一个词。这是宁波方言,说的是勤俭持家。这种风气,贯穿于老宁波的日常生活。 他从小听大人们讲起,过去宁波人日子清贫,吃饭吃菜厉行节约。 一份蟹糊摆上桌,用筷子尖蘸了,唯恐过多,还要甩上几甩,才肯放进嘴里下饭。 抑或三颗泥螺过一碗热泡饭。老宁波骨子里的“做人家”,在饮食上体现得近乎极致。 再比如,他说宁波人吃早餐,有“四大金刚”:大饼、油条、粢饭、豆浆。最省事的还是泡饭。 几乎每个宁波人都是吃泡饭长大的。泡饭与粥不同,是由隔夜的冷饭加水煮成。 它没有粥的黏糊缠绵,一粒一粒,颗理清晰。 如此寻常的东西,柴隆还一头扎进故纸堆,寻觅泡饭的历史: 泡饭最早可能诞生于五代,其学名曰“水饭”。南唐刘崇远《金华子杂编》中,就有“水饭”的记载。 吴自牧的《梦粱录》和周密的《武林旧事》中,都曾有关于泡饭的记载。 柴隆描述老宁波人做泡饭的情景,是一幅远去的市井画面: “无数个清晨,老墙门内的主妇们揉着惺忪的睡眼,穿着睡衣,趿一双拖鞋板,晃晃悠悠下楼来到灶跟间,捅开封了一夜的煤球炉,坐上一个钢精锅子,取下吊在灶梁顶钩上的‘饭篮筲箕’,抓入几块隔夜的‘冷饭娘’,倒入热水瓶中的开水,盖上锅盖任其滚煮,然后忙着去倒马桶……” 泡饭其实说白了就是回锅的剩饭,省时省力,一碗水泡饭,几分钟搞定,没什么营养。 可就算是旅居海外的宁波帮,经常在外应酬,荤腥吃多了,最爱的,还是那一碗热乎爽利的泡饭。 【压饭榔头】 压饭榔头,通俗点说,就是下饭神器。 宁波人的压饭榔头很多,大多是宁波人尝了鲜掉眉头、外地人看了皱紧眉头的海味冷盘,诸如醉泥螺、蟹糊、血蚶、生蛎黄等等。 在柴隆眼里,最下饭的要数醉泥螺,肚皮撑破还要讨。醉泥螺过泡饭,呼噜呼噜能吃一大碗。 柴隆对腌泥螺也颇有研究。他认为泥螺腌制入食,以三季为佳:“三月桃花盛开,泥螺壳软味美;五月梅雨淅沥,泥螺膏溢壳外;中秋桂花满地香,泥螺莹若水晶,爽脆滋味长。” 吃泥螺,吐泥螺壳,在他笔下也变成一件诗意的事:“把螺肉吃下,将薄如蝉翼的白壳吐出,竟似口吐莲花一般。” 在柴隆看来,能与泥螺平分秋色的是蟹糊。泥螺与蟹糊,搭配泡饭最适宜,好比宁波话里的阿青与阿黄。 老宁波人都会自制蟹糊,但最让柴隆痴迷的是坊间流行的“活蟹十八斩”。 活的梭子蟹,腌制只消几分钟,筷子夹一块,含在嘴唇之间,用舌尖顶住蟹壳,“嘴唇轻轻地抿吮,‘嗦’的一声,一粒鲜美的蟹肉就顺着舌尖到了口中,细细咀嚼,清香脆嫩,丰腴可口,甜甜的蟹肉中溢着酒香。”“吃过几块,过半天,咂咂嘴,舌尖唇边还透着鲜气。” 看他的描述,似乎那蟹肉已沾到舌尖,滑过喉咙,鲜咸荡漾在唇齿间。 【好吃场】 书里描绘的不仅是宁波传统小菜,还有宁海、鄞州、奉化、余姚、慈溪、象山一带独有的乡野风味。 宁海有句土话:“长街的蛏,胡陈的桃,越溪的弹涂把舞跳;岔路的饼,茶院的面,一市的白枇杷实在甜。” 朗朗上口的顺口溜里,道出了宁海的风物。但宁海的“吃场”(吃食)绝不仅限于这几样。 最让柴隆震撼的,是宁海人吃百家馏的场面,俨然当年戚家军被村民们拥着吃馏的场景。 明嘉靖年间,戚继光曾亲率主力,在宁海一带日夜指挥追剿。 正是春寒料峭的季节,戚家军遵守“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军纪,肚子早已憋塌,却只能忍饥挨饿。 宁海村民看到此情此景,纷纷拿出不多的杂粮、菜、肉,混在一起,煮成羹糊,凑成百家馏,送去前方。 将士们喝完百家馏,士气大增,一鼓作气,击退倭寇。 自此,正月吃馏,成了宁海习俗。百家馏,既可当主食,也可下饭。 余姚黄鱼面,也是柴隆偏爱的美食。照理说,余姚不靠海,不出产黄鱼,但余姚人不经意间与黄鱼结缘,倒是造就了一段佳话。 上世纪50年代,野生黄鱼物美价廉,余姚舜江楼旁,有个三阳酒家。 一位姓王的名厨,尝试着把新鲜黄鱼与面同烧,结果鱼香四溢,肉嫩面滑,汤味浓醇,顾客吃了以后赞不绝口,回味无穷。 此后,各处餐馆纷纷效仿,余姚黄鱼面的名声,也渐渐传开了。 柴隆不仅考证出余姚黄鱼面的缘起,还摸熟了吃黄鱼面的去处。 除了南塘老街的余姚黄鱼面馆,在余姚当地,太平洋酒店边上的“鲜得来”、长安路上的“松兰”、健康路的“阿玉面馆”、东旱门路的“黄鱼面馆”、北滨江路的“何记”等等,都能吃到正宗的余姚黄鱼面。真正比当地人还如数家珍。 【书籍推荐】 文章节选: 宁波人吃年糕,花头多,样式也常翻新。从原始的“火缸煨年糕”到“咸齑冬笋年糕汤”,从“大头菜烤年糕”到“菠菜毛蟹炒年糕”,无固定的程式,时令菜蔬、海鲜皆可搭配,吃法屡见奇特与创新。 譬如央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中,给了一盘“梭子蟹炒年糕”一个特写镜头。当梭子蟹贱到白菜价的时候,鲜到根本无需放味精,用它炒年糕是广受街巷欢迎、又最具本土特色的。蟹块与年糕红白相间,点缀些姜丝和葱段,螃蟹与年糕的相逢,“目食”与口舌皆得,这是宁波人匠心独具的家常美味。宁波人饮食的巧致,在这盘“梭子蟹炒年糕”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段水磨年糕的风雅,藏于市井生活中,体现在日常饮食里。 《宁波老味道》,柴隆著,宁波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