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川剧《红梅记》
|
 |
《李慧娘·放裴》
|
 |
《红梅记·杀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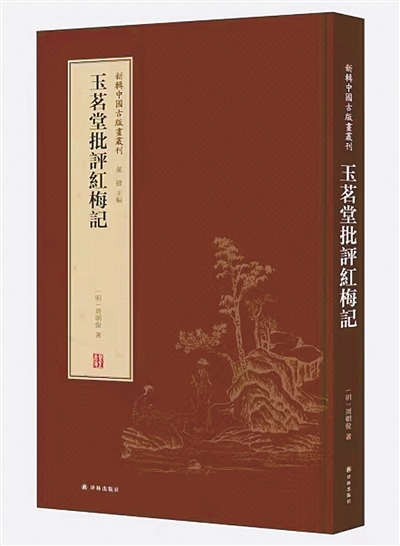 |
《玉茗堂批评红梅记》
(新辑中国古版书丛刊)
|
 |
《绣像红梅记》(清代成和堂藏本)
|
 |
袁宏道刻本《红梅记》
|
 |
鄞江镇光溪村(周朝俊出生地)
|
假如为宁波戏曲的传世之作列一个排行榜,第一名自然是《琵琶记》。可作者高则诚却是永嘉瑞安人,他客居栎社时,在瑞光楼上伏案执笔,遂成大作。而由正宗阿拉宁波人撰写戏曲剧本、在戏苑艺坛上流传时间最长、登台演出场次最多、影响力最大的曲目,应该是《红梅记》。 乍一听,这剧名有点生疏,可说到它的改编本京剧《李慧娘》(早期系昆曲本),知道的人就很多了。至今,高腔、皮簧、梆子系统的地方戏曲剧种里,均有根据《红梅记》改编的剧目,如川剧《红梅阁》、河北梆子《阴阳扇》、秦腔《游西湖》、粤剧《再世红梅记》等几十种。此外,《红梅记》中的一些场目,如《游湖》《幽会》《鬼辩》也成为戏曲折子戏经典而长演不衰。 《红梅记》的作者,是活跃于明隆庆、万历年间的鄞县人周朝俊。 生卒不详的周朝俊 周朝俊的生平,在史料上没有翔实记载,甚至他的生卒年月,在《中国戏曲志》中也仅仅是“不详”两字。可说到他的籍贯与出生地,所有史料都真真切切地写着鄞县(今浙江宁波市)人。清代鄞县乡贤李邺嗣先生,就在他的《甬上耆旧传》里写道:“周文学朝俊,字夷玉。少有才,为诗慕李长吉,亦工填词。所撰有《李丹》《香玉人》《红梅花》十余种,唯《红梅花》最传。”这其中提及的《红梅花》剧名,大概是他的一个笔误,《红梅花》即是《红梅记》。 明代文人王稚登曾为《红梅记》作序,文字比较详尽,写了当年周朝俊在西湖边上宿寓题诗、萌发撰写《红梅记》的创作动因,以及他执笔完稿后的愉悦心情。序云:“四明周生者,余初未尝识。乙酉秋,余复有西湖之游,宿昭庆上人房。偶于壁上见所提诗句清宛,后有生名,余叹赏之。上人云,此生仰王先生非一日矣,今亦寓敝刹。先生倘有意乎,弗靳一面,以慰生夙志可乎。余曰,所作如此,其人可知。遂嘱上人邀之同席。观其举止言笑,大抵以文弱自爱。而一种旷越之情,超然尘外。余次过其寓中,见几上一帙,展视之,乃生所制《红梅记》也。循环读之,其词真,其调俊,其情宛而畅,其布局新奇而毫不落于时套。削尽繁华,独存本色。嘻,周郎可谓善顾曲焉。”细读这一段来自同时代文人的记录,仿佛周朝俊就站在面前,他以一种“旷越之情,超然尘外”的神态与举止言笑,让人感到十分亲近,久久难以忘却。尤其是文中最后几句评价《红梅记》的赞言,写得特别到位,特别传神:“其词真,其调俊,其情宛而畅,其布局新奇而毫不落于时套。”正因为如此,《红梅记》一出世就成为“爆款”,风靡于明代的梨园戏台。 周朝俊年少就颇具才学,擅长作诗填词,虽说博学多闻,句法清婉,但仍是乡间一名秀才而已,平生从未考取任何功名,终身布衣,他以诸生自娱为乐。在我国古代,没有做官的文人总是沉沦下层,难入史册。因此,《鄞县志》里没有他的传记,就连历代考生名录里也找不到他的名字,甚至还被逐出了家谱! 编辑《中国戏曲志·浙江卷》期间,为了弄清周朝俊的生卒年月,撰写这项条目的供稿者,先后查阅了《四明章溪周氏宗谱》《半浦周氏支谱》以及《象岩周氏宗谱》等多部周氏家谱,未见录有周朝俊名字者,唯独在《四明光溪周氏宗谱》里发现有“朝”字辈载录,而且都生于明代。光溪村位于西乡鄞江镇,与著名的它山堰近邻,鄞江镇古称“四明首镇”。《四明光溪周氏宗谱》里记载,第十代世祖周懋公的长子周朝文,字履美,号仰峰,生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同辈人中还有朝恩、朝礼、朝辅、朝卿以及朝炯等20余人。有人提出,朝炯系朝俊的同音字误,是第十代世祖周懋公的幼子,可此事又无旁例可证。尽管如此,却可以推断,周朝俊就在“朝”字辈里,他的出生年月,估计是在隆庆年间(1567年前后)。 至于周朝俊卒于何年?这在周氏家谱中更是难以查考了。所幸后来意外发现他遗留的一首诗篇:“白雪下葳蕤,饥乌隔树窥。先生眠未起,小子立多时。骏骨伤寒素,春姿老冻梨。痴奴不解事,呵手弄冰丝。”这首诗的篇名是《雪中候屠田叔先生门》,屠田叔即是明代万历年间一位儒学名家,姓屠名本畯,字田叔,也是鄞县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曾以父荫任太常寺典簿、礼部郎中以及湖广辰州知府。后因鄙视名利,离职返回故里,写过许多有关农、渔、茶的书籍,是我国早期植物学与海洋动物学的一代名师。另外,屠本畯也写过一本单折曲目《饮中八仙记杂剧》,因而与周朝俊有了交往,并有师生之谊。明代天启年间,屠本畯与友人张庚星、李大缔等九人结九老之会,皆布衣处士,各赋诗以畅老怀。周朝俊也是九老会成员之一,此时他已是一位六旬老人。 又据屠本畯《甬上屠氏家谱》中记载:“公七十大寿庆演《饮中八仙记杂剧》。自扮剧中人太憨生,令周朝俊杂扮吕洞宾等人。”由此可见,周朝俊既擅长填词作曲,又能客串演戏,也许他就是梨园中人,曾为良家子弟后沦落为戏子,因此,家谱不把周朝俊纳入其内,也就不足为奇了。 双线奇构的《红梅记》 《红梅记》整台戏计34出,由两条爱情线索交织而成。主线是南宋杭州城里的一介书生裴禹与卢府小姐卢昭容的婚恋过程,副线则写奸相贾似道的侍妾李慧娘与裴禹的生死之情。后来,由于李慧娘这个不畏强暴、富有正义感的倔强女子越来越受到观众喜爱,副线渐渐超越了主线,成为《红梅记》中最动人的乐章。 周朝俊撰写的《红梅记》,取材于他的同时代人瞿佑《剪灯新话》中的《绿衣人传》。李慧娘与裴禹的情节线索原在《绿衣人传》中有所记叙,但在《红梅记》中作了大量渲染,发展成一个独立的故事,也是全剧中最能体现作者艺术才华的地方。《远山堂曲品》说它“手笔轻倩,每有秀色浮动曲白间,当是时调之隽。其语言科诨不俗,直刺世情。”李慧娘这位叛逆的女性、屈死的冤魂,以她死而不灭的仇恨与挚爱,化作惊天动地的果敢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和仰慕。 《红梅记》一剧分上下本。李慧娘的故事至上本而结,下本围绕裴禹和卢昭容的故事展开,回目清晰,但精彩程度不及上本。剧作从李慧娘随同贾似道泛舟西湖开篇,湖中偶遇年少英俊的裴禹,李慧娘不禁失口赞道:“呀,美哉一少年也!”谁知只是这一句话,就让奸相顿生杀意。回府后贾似道立斩李慧娘,还丧心病狂地用金盆盛头,让众姬妾逐一观看,杀一儆百,其后又把李慧娘的尸首埋于花树之下。不久后,那奸相又看中了卢府小姐的美貌,欲夺卢昭容为妾。卢夫人为了抵制贾似道的淫威,抢先招裴禹为婿。这件事更加激怒了奸相,于是设计囚禁了裴禹,欲暗害之。幸得李慧娘鬼魂相救,掩护裴禹逃出贾府。后贾似道兵败襄阳,被朝廷所贬,途经漳州木棉庵,为会稽尉郑虎臣所杀。裴禹逃出贾府后,应试临安,擢探花,与卢昭容历尽坎坷结为夫妻,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李慧娘在《红梅记》里虽非主角,但塑造得十分出色。周朝俊通过《游湖》《杀姬》《幽会》《放裴》等诸折子戏,把她善良多情、富有正义感、不畏强暴的性格表现得光彩动人。裴禹当时被贾似道软禁于半闲堂书馆,当夜二更,李慧娘的鬼魂立在书馆前叩门。裴禹以为是贾似道设下的美人计,将对方拒之门外。李慧娘告知实情,嘱咐裴公子快快逃走。裴公子感念慧娘真情,不肯一人逃走。两个身影在夜色中离合纠缠。此时此刻,李慧娘一身白衣,水袖翩飞,白绫翻覆,诉尽离情,与裴公子做最后告别:“劝裴郎切莫为我轻生,我怎不愿阴曹地府结同心,你若为徇私情舍了命,岂不是辜负了你美哉少年这一生。你应当以国为重除奸贼救黎民,到来日一炷清香三杯酒,红梅阁旁听一听,当闻我九泉下含泪笑声。”此即为《幽会》一折。在随后的《鬼辩》一折中,李慧娘怒斥奸相的无耻与残暴,大胆地唱出了“贼子呵!俺残魂只索把花根傍,哪知你又向人间魅裴郎。”这种超越了生死界限的情感,可以战胜一切。 《红梅记》以一支红梅作为剧名,实是来自毫不起眼的一个细节。 一日,裴禹路过湖边宅邸,看墙内红梅开得正好,想攀墙折一枝把玩,谁知却一骨碌翻落墙头。总兵之女卢昭容早在墙内把一切看得清楚,她吩咐侍女:“正巧我鬓边有枝红梅,你拿去给他吧。”由此引出了一系列撼人心魂的故事。 周朝俊在《红梅记》中宣扬“一身虽死,此情不泯”,爱情可以超越生死界线,可以战胜黑暗势力的迫害和摧残,这与汤显祖《牡丹亭》所表现的思想有相近之处。 中国戏曲史上,有两个因情而死、死而不已的女性形象:一个是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塑造的杜丽娘,她因情而死,缘梦相会,由情复生,与心上人柳梦梅鸳梦重温;另一个便是周朝俊在《红梅记》里创作的李慧娘。 出圈即网红,冰火两重天 周朝俊虽然终身布衣,混迹梨园,受到同宗族人的冷落,但在当时文人圈里却大受欢迎,尤其深受优伶戏子的喜爱,纷纷搬演《红梅记》不息。明万历年间,就有广庆堂刻印的《红梅记》刊本问世,继有袁宏道的删订本以及玉茗堂评刊本、剑啸阁刊本等多种。《甬上耆旧诗》里记载:“每宴客,伶人莫不唱《红梅记》,其为盛世传曲若此。” 相传周朝俊在世时,曾有一位好友名叫李玉海,获任四川蜀山县令。临别时,周朝俊与伶人们一道粉墨登场,送好友上任,从而使《红梅记》一曲,从江浙一带唱到了四川,以致后来成为川剧传统名剧之一。《红梅记》人鬼同台,给川剧表演提供了很大的创造空间,让“变脸”“喷火”以及“走碎步”等许多绝招有了用武之地。尤其是“喷火”这一项绝招,更是广受好评。这火怎么喷呢?道具师傅要提前现做一个“包子”(梨园行话)。“包子”的馅是松香粉,皮是透气性很好的纸,包两层,像鸡蛋这么大。然后剪一个孔,让演员含在嘴里。表演“喷火”在著名的《放裴》这一出戏里,奸相贾似道派杀手廖莹中去干掉裴禹,正要下手之际,李慧娘鬼魂出现了。这时,扮演李慧娘鬼魂的演员要迎着火把,变着花样喷火。先是短喷,站在杀手的腿上,喷得威武有力。然后是引火,从左到右,喷一个横条,煞是好看。最显功夫的还是最后一个长喷,演员要仰起头,来一个360度鹞子翻身,再怒瞪双目,张大嘴巴,用力喷火,眼前一片红火。每逢表演到此处,戏台下就会爆发雷鸣般的掌声。 《清中叶戏曲家散论》中评价周朝俊时写道,“夷玉宣身虽死,情不泯”。这寥寥数语,就道出了《红梅记》的影响力! 新中国成立后,《红梅记》很快进入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视野。1959年,广东作家唐涤生首先将《红梅记》改作《再世红梅记》,演出于粤剧舞台。同年,北方昆曲剧院约请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著名作家孟超把周朝俊《红梅记》改编为昆曲剧本。孟超很喜爱李慧娘这个艺术形象,给予高度赞扬。他说:“我则终以为生前受尽压迫凌辱,白刃当前,渐露与权奸拼死斗争之机,染碧血,断头颅,授死不屈,化为幽魂……如此扬冥冥之正义,标人间之风操,即是纤纤弱质,亦足为鬼雄而无惭,虽存在于无何有之乡,又焉可不大书特书,而予以表彰呢?”基于这种指导思想,孟超广泛搜集和研究了有关李慧娘的历代剧稿,伏案执笔,于1960年春夏之交完成了《红梅记》的改编本昆曲《李慧娘》。 1961年8月,北方昆曲剧院在首都舞台演出《李慧娘》,受到社会广泛的好评,也深为戏剧界、评论界所称道。《人民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称《李慧娘》“个性以辣,风格以情”。更有人赋词以赞:“孟老辞章,慧娘情事,一时流播京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时任北京市统战部部长的廖沫沙先生以“繁星”为笔名,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有鬼无害论》文章。廖沫沙写道:“看过孟超同志改编的《李慧娘》演出,人们都说这是一出好戏,不但思想内容好,而且剧本编写得不枝不蔓,干净利落。比原来的《红梅记》精炼,是难得看到的一出改编戏。”又说“我们中国的文学遗产(其实不只是中国的文学遗产)小说、戏曲、笔记故事,有些是不讲鬼神的,但是也有很多是离不开讲鬼神的。台上装神出鬼的戏,就为数不少。如果有人把传统的戏曲节目做个统计,有鬼神上台或鬼神虽不上台,而唱词道白与鬼神有关的节目,即使占不到半数,也总得占个几分之几。这类戏,如果把中间的鬼神部分删掉,就根本不成其为戏了。试想,《李慧娘》或《红梅记》这出戏,如果在游湖之后,贾似道回家就一剑把李慧娘砍了,再没有她的阴魂出现,那还有什么好看的呢?” 然而仅仅隔了三年,现实的“剧情”突然出现一个大反转。1964年7月,孟超的昆曲《李慧娘》和田汉的京剧《谢瑶环》、电影《早春二月》等一批文艺作品,被打成“大毒草”。而《李慧娘》开了批判一系列“鬼戏”的先例,被禁演……粉碎“四人帮”后,北方昆曲剧院恢复了建制,重新演出了《李慧娘》,并将其作为保留剧目。 昆曲《李慧娘》成为当代文化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 一个迟到的建议 周朝俊死后的寂寞是令人心酸的。据一些零星史料透露,他一生创作的传奇有十余种之多,至今知道名字的就有《李丹》《香玉记》《画舫记》数种,但几乎失传,未留下完整剧本,甚为遗憾。倘若这些曲目能一直流传至今,与《红梅记》一起绽放,交相辉映,中国戏曲定会以更加凄美艳丽、想象奇特的面貌,展现在千千万万的世人面前! 周朝俊的出生地光溪村位于鄞江镇中心,村以一条水声潺潺的溪流命名,两岸民居耸立,风景秀美。 笔者不妨提一个建议,假如四明光溪周氏族人重修家谱,千万别忘记把周朝俊这个名字补上,或在村口立一座周朝俊雕像。再也不能让传世名作《红梅记》的作者,久久湮没在历史尘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