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百孝图》中的沈起弃官侍父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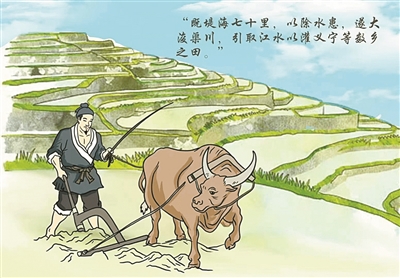 |
| 沈起率民众开沟挖渠,发展农业。(图片来自南通发布) |
 |
| 宋越熙宁战争概述图 |
 |
沈起画像(图片来自浙江省纪委监委网站)
本版图片由祝永良提供 |
祝永良 他在江苏海门筑海堤、治水患,施良政、惠百姓,得到包拯举荐、王安石称颂。他与王安石同榜进士,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一生都在践行以民为本、富国强兵的思想。然而,他的名望与辉煌,却在宋越熙宁战争中画上了句号,大文豪苏轼的一纸奏疏,更是给年近七旬的他致命一击。宋以后史料记载中,也常常视他为引发宋越熙宁战争的祸首。而令人欣慰的是,在江苏海门,老百姓至今仍在称颂这位泽被千秋的好官。 这位功过是非任由评说的官员,就是宋代鄞县人沈起。他与王安石之间的一段渊源,也成为中国县域治理史上的一个样本。 同榜进士同入仕途 沈起(1017年-1088年),字兴宗,明州鄞县人。沈括在《故天章阁待制沈兴宗墓志铭》中,说他“少笃学,有闻州闾”,系“州举进士第一人”。 宋庆历二年(1042年),26岁的沈起与22岁的王安石同登进士榜。之后,王安石被任命为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沈起则担任滁州判官,同时监真州(今扬州仪征)转般仓(调运漕粮的仓库)。 很快几年过去了,沈起在任上干得顺风顺水,可就在这时,传来了他父亲患重病的消息。 沈起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着急,恨不能马上回家。但按照宋朝制度,地方官除非任期已到、父母亡故或奉有特旨,一般不能离开任职所在地。想请假,要走很多流程,得很长时间才能审批下来。 沈起回家心切,干脆弃官挂印、不辞而别了。父亲见到儿子,喜出望外,病情有所好转。但没过多久,父亲还是去世了。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沈起悉心照料,尽到了为人子的一片孝心。 沈父去世的第二年,也就是宋庆历七年(1047年)春天,王安石调知鄞县。两人在明州见面,自是一番感慨。王安石被沈起的孝心感动,提笔为沈父作《太子中舍沈君墓志铭》,铭文如下: 沈氏世家吴兴,其后有陵者仕吴越王,卒官明州,家之,五世而生公。 公讳兼,字子逵,以五举进士得同学究出身,再补尉,有能名。用举者迁卫尉寺丞、知湖之归安县,移知邵武之归化,又有能名。迁太子中舍,通判苏州,其以能闻愈甚。公好刚,遇事果急不顾计。为通判日,与守争可否,不为之小屈。重犯转运使,使、守相与害公,入之法,除名,天子薄其罪,免所居官而已。公归怡怡,间为五字诗自戏娱,无躁戚言。卒于家,年七十三,庆历六年七月也。 子男一人,起;女三人。起好学,通政事,能守节法,为进士,与某同时得科名者也。公之坐狱,为判官滁门,立弃官从公,世以为孝。将以某年某月葬公某处,以夫人柳氏祔,先三月来求铭。与铭曰: 生也不得,其须而死。死也何有,有嘉者子。呜呼,已矣夫! 沈起守丧期结束后,按照宋代的“保举”制度,包括王安石在内的很多人希望他出来做官。但沈起的上司因为他曾经擅离职守,上疏弹劾,要朝廷治他的罪。宋仁宗了解到沈起辞官的真正原因后,作出了“观过知仁”的结论,认为从沈起的过失中可看出他是个仁义之人,应该原谅,于是不但没有治沈起的罪,还任命他为海门知县。 筑堤挡潮志除水患 江苏海门,滨江负海。史载,大略公元前后,大量泥沙沉积于长江口。至唐末,形成了扶海洲、胡逗洲、南布洲、东布洲等沙洲。宋代,东布洲与大陆之间已经有沙滩涨起,由于海岸线逐渐外移,老百姓为图生计,纷纷前往开发农灶煮盐,人口不断集聚。但由于地势低洼,海潮、江水常常漫过堤岸,特别是一遇到大水,这些低洼地段就会被水淹,老百姓庐舍漂没,田灶毁坏,家破人亡。明嘉靖《海门县志》记载,自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年)海门置县,海门人一直“与江海争壤于涛澜茹吐”。 公元1054年,北宋至和元年,当37岁的沈起来到海门时,出现在他面前的正是这样一副凄凉的场景。面对莽莽草荡,滚滚海浪,雄心勃勃的沈起决定在东布洲与通州大陆间筑起一条拦海大堤。这条长堤东起吕四廖角嘴,西至余庆场西北角。 为筑好海堤,他总结前人筑堤的经验,在堤址的选择上“移堤势而西,稍避其冲”,就是让堤址尽量离潮水远一些,潮水到时水势减弱,以增强海堤的安全性。 他亲自勘察,确定堤线。在一次大潮之前,他让百姓将稻壳撒在漫长的海滩上,涨潮时稻壳上浮至岸边,依此打桩定线。堤基顺水势“纡斜迤逶,如坡形,不与水争”,弯弯曲曲以增加抗浪能力。 他自任监工,每天亲临施工一线。经过两年多时间,一条长达70里的海堤终于建成,从此,海门万亩良田不再受海潮侵扰,保证了大批盐民开灶煮盐。 为使百姓安居乐业,沈起还加大农田水利建设力度,对境内原有的河道进行疏浚,增加其蓄水和通航能力。同时率民众开沟挖渠,引进江水,灌溉农田,增加粮食产量。 沈起还上疏朝廷,希望通过缓征税捐的办法,吸引外出流民回归海门。朝廷批准了他的这一请求,流落在外的海门人纷纷返家,商贾闻讯也争相来海门经营。由此,海门这个海边小邑人丁兴旺,物产丰饶,市场繁荣,富甲一方。 沈起主持修筑的海堤,后来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沈公堤”,直到今天仍是海门的一道人文风景线。 包拯举荐荆公称颂 沈起在海门的政绩,很快传到了京城,传到御史中丞包拯耳中。包拯认为,像沈起这样的栋梁之材应该受到重用,于是推荐沈起为监察御史。海门当地有一种说法:包拯还让王安石接替沈起,到海门任知县。 这个说法出自明嘉靖《海门县志》。该志记载: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擢进士第,签书淮南,至和中为海门令,治声藉甚。后遇神宗,位至宰辅。卒,谥曰文。 王安石任海门知县一事,《宋史》等史籍没有记载,清代学者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也没有记载。但王安石为海门写过一篇《通州海门兴利记》是可以肯定的。这篇记全文如下: 余读豳诗:“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嗟乎!豳之人帅其家人勠力以听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也。夫喜者非自外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既叹其吏之能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则亦欲善之心出于至诚而已,盖不独法度有以驱之也。以赏罚用天下,而先王之俗废。有士于此,能以豳之吏自为,而不苟于其民,岂非所谓有志者邪? 以余所闻,吴兴沈君兴宗海门之政,可谓有志矣。既堤北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酾取江南,以灌义宁等数乡之田。方是时,民之垫于海,呻吟者相属。君至,则宽禁缓求,以集流亡。少焉,诱起之以就功,莫不蹶蹶然奋其惫而来也。由是观之,苟诚爱民而有以利之,虽创残穷敝之余,可勉而用也,况于力足者乎? 兴宗好学知方。竟其学,又将有大者焉,此何足以尽吾沈君之材,抑可以观其志矣。则论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书之,今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遗其民而不愧于豳之吏者,果多乎?不多,则予不欲使其无传也。至和元年六月六日,临川王某记。 沈起祖籍吴兴,故王安石称其为“吴兴沈君兴宗”。在这篇记中,王安石用《诗经·豳风》里的诗句“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来表达百姓服从官员的安排、官员根据民意来管理百姓的理想状态。随后又通过赞扬沈起修大堤,让百姓受惠,注重民生等事迹,来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以及他对基层工作的理解。 这篇记,与王安石后来提出的变法主张有许多共同之处,如“君至,则宽禁缓求,以集流亡。少焉,诱起之以就功,莫不蹶蹶然奋其惫而来也”。意思是说:沈起到海门后放宽禁令缓征捐税,召集流民回乡,首先确保这些乡民生活安定,再引导他们兴修水利,恢复生产,这样就使老百姓很快振作起来,鼓起重建家园的信心,一心一意投入到兴修水利中去。而这些,正是王安石“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的变法思想的核心。 王安石认为,沈起的官虽然小,但他做的事情非常重大,整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很小的县,一个个很小的县官组织起来的,如果每一个基层官员都能像沈起那样为民谋利,那整个国家老百姓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 王安石与沈起,都是青年进士,都当过知县。在沈起出任海门知县之前,27岁的王安石已在其主政的鄞县组织民工整治广德湖、东钱湖,除葑草,浚湖泥,立湖界,置碶闸、陂塘,筑七堰九塘。还在今北仑穿山区域凿山为碶,捍浦为河,治理芦江,变荒滩为良田,化水害为水利。 或是受王安石启迪,沈起到海门后也全力兴修水利。当沈起修水利初见成效时,王安石立即风尘仆仆来到海门,写下这篇记加以推崇,从中可见两人志趣相投。后来,沈起赴湖南就职,王安石还作《送沈兴宗察院出使湖南》一诗相送: 谏书平日皂囊中,朝路争看一马骢。汉节饱曾冲海雾,楚帆聊复借湖风。皇华命使今为重,直通酬君远亦同。投老承明无补助,得为湘守即随公。 政声卓著平叛果断 沈起离开海门后,先是任监察御史,后又任京东路提点刑狱、开封府判官、湖南路转运使、三司盐铁副使、天章阁待制等职,任内政声卓著,受到朝廷赏识。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作为变法的坚定拥护者,沈起无疑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 这年,西夏大举入侵北宋西北地区,宋神宗派韩绛为陕西宣抚使,开幕府于延州(今延安),并由沈起任陕西转运使。 韩绛不习兵事,举措多有失误。他先是在罗兀(今陕西榆林境内)筑城,又冒雪筑抚宁堡。不久,两城均遭西夏猛攻。韩绛命各道宋军出援,因用人失当,没能妥善处理番兵与原驻军间的关系,引发庆州兵变。 虽然叛军很快被沈起率军讨平,但由于兵变的爆发,宋军不得不放弃罗兀城和抚宁堡,宋朝进取横山(今陕西榆林西南)的计划因此受挫。事后,韩绛被罢相,沈起贬知江宁府(今南京)。但没过多久,沈起又被召回,提举在京诸司库务、知吏部流内铨(专主州县官吏的考课事务)、三司度支副使(掌财政)。 其间,他奉命出使辽国。辽方有意将宋使的座位和西夏使者安排在一起,沈起据理力争:“西夏对宋称臣,他们的使者不过是陪臣,怎么能和宋天子的使者同坐?”他见辽方首鼠两端,就坚决拒绝就座。辽方没办法,只好将夏使逐出,把宋使的地位升高,并从此定为制度。这样,沈起有力维护了宋朝的大国尊严。 经略广西整饬防务 熙宁六年(1073年),正是王安石变法的关键时期,新旧两派争斗十分激烈。节骨眼上,广西边境线上形势紧张了。沈起临危受命,任广南西路经略使,兼知桂州(今桂林)。 当时的情形是,南方的交趾(越南北部)借口追捕逃犯,多次入侵钦州、邕州(今南宁)所属边关羁縻州峒,抢夺财物,焚烧民房,杀人越货。宋朝尽管对交趾北犯非常愤怒,但鉴于北方有强辽悍夏窥伺,也只好对交趾采取一些怀柔政策,无暇提升相应的防卫力量。 沈起到任后,着手对边防事务进行一系列改革。他收编当地部落民众,把他们组织为保甲,授以阵图,使其在农闲时练习作战。同时派一些曾习水战的将吏前往海滨,教习水战。暗地里,他还部署制作战船。 当时,交趾人常常借到广西各州县贸易之机,窥探宋军虚实。如交趾李朝派在广源州的军将刘纪,曾多次向广西经略安抚使司提出请求,要在邕州境内的太平寨与宋军进行贸易,其用意就是想乘虚而入。 山雨欲来。沈起洞察到了这些苗头,规定从今以后禁止交趾人入境。 这时,邕州知州苏缄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章,大意是:交趾与大宋关系紧张,源于沈起对交趾政策。下臣以为要缓解两国关系,边贸不可废也。另,交趾野心勃勃,邕州兵少将寡,请皇上速派兵增援。 皇帝回复:沈起边境练兵、关闭边贸确有不妥。朕已决定将他调走,桂州知州由刘彝继任。眼下,辽和西夏虎视眈眈。卿宜按兵固守,毋得贪功轻敌……” 刘彝到了桂州,觉得沈起并没什么过错。大敌当前,沈起落实的防卫措施不但不应该废除,而且应该强化。他听说沈起是因为被苏缄告到皇上那儿才被调走的,就对苏缄有了成见,反过来弹劾苏缄“沮议”。 但刘彝的确低估了交趾的无耻。熙宁八年(1075年)十一月,交趾李朝又一次以追捕叛军为由,集结兵力,向北宋的广东广西边境发动大规模进攻。 交趾大军所到之处,都在大街上张贴《露布》“声讨”北宋政府,其中一条是:“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今我出兵,欲相拯济。” 就是凭着这样的借口,交趾李朝在这一年的冬季三路进兵,一路攻下钦州,一路攻下廉州(今广西合浦县),另一路围困邕州。由于兵力悬殊,邕州城在坚守42天后陷落,通判唐子正战死,知州苏缄自焚殉国。交趾兵入城后,将5万多名老百姓全部赶进邕江杀死淹死。 消息传到汴京,朝野震动。很快,宋廷发出《讨交趾敕谕》,调山西、陕西两地十万禁军精锐南下,集军民30万浩浩荡荡进入广西,突入交境,与交趾军大战于富良江(今越南红河),斩杀交趾王子李弘真、李昭文,交趾君主李乾德奉表乞和。 宋军由于冒着炎热进入瘴疠之地,伤亡同样惨重,军粮耗尽,虽一水之隔也很难再进。于是,双方议和。 关于熙宁战争,后世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冗官、冗兵、冗费及由此带来的积贫积弱,是构成北宋中期社会危机的重要因素。交趾统治者正是看穿了宋朝的外强中干,才敢如此轻举妄动。 担责受贬郁憾而终 在这场血战爆发前,沈起的桂州知州职务已由刘彝接替,他先是调知潭州(长沙),几个月后又移知杭州。战役结束后,沈起被诉“妄传密受朝廷意旨经略讨交州”(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二);刘彝被责“相继生事”,令交趾“疑惧为变”。于是,刘彝免官,徙涪陵。沈起被降为郢州团练副使。后遇赦,移知秀州(嘉兴),接着又移知温州。 在事情过去十年以后,到了元祐元年(1086年),战争的创伤已经得到医治,刘彝被朝廷起复为都水丞。朝野上下都认为沈起将再度受到重用,皇帝也有这个意思。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大文豪苏轼一纸《缴进沈起词头状》,彻底掐灭了沈起复出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给了年近七旬的沈起致命一击。 苏轼此文,不仅将安南之役的责任全部推向沈起、刘彝,还将矛头直接指向王安石。对沈起的品行更是极尽贬损。 他认为造成熙宁战争的直接原因是沈起和刘彝言行不当,根源在王安石好大喜功。指责变法派不仅破坏了宋越关系,而且将宋朝与当时其他并列政权的关系都搞得很紧张。 不仅如此,苏轼此文还直接伤害了包括其好友章惇在内的一大批人。招抚西南,平定五溪蛮,本是章惇最得意的政绩,熙宁年间苏轼还专门写诗赞美。而这一次,为了打击新党,苏轼不惜倒戈相向,彻底否定了章惇的功绩,将他指责为“结怨交蛮,兵连祸结”。这种在新旧党争中不理性的态度以及“矫枉必过正”的行事方式,不仅让沈起深受其害,还让苏轼与好朋友章惇等之间的友谊产生了极大的裂痕,也为他自己在绍圣年间被贬惠州、儋州(今海南岛)埋下了伏笔。 这一年,66岁的王安石黯然病逝于江宁。两年后,71岁的沈起也于苏州郁憾而终。 沈起与王安石,两人的命运很接近,都是青年进士,都当过知县,都在兴修水利方面为民造福、声誉卓著,都有富国强兵的政治志向,后来又都荣升,而最终他们都是黯然离场。其功其过,后人各有评说,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他们的县政发展理念,在中国县政治理史上始终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