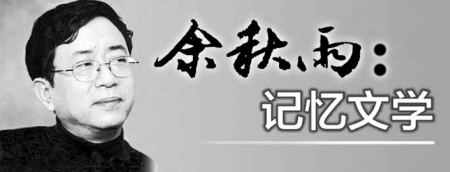 |
| 61 |
我一看,那是一份南方有名的周报,文章的标题很长,叫做《“文革”可以被遗忘,却不可以被掩盖》,作者正是曾远风,我吃惊地匆匆看了几眼。曾远风在那里愤怒地写道,有人要掩盖“文革”罪行,他绝不答应,一定要战斗到底。 徐扶明教授告诉我,曾远风在好几年之前就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变革”的批判者。很多读者把他当作一名反“文革”的英雄好汉,完全不知道他在“文革”中是如何让人闻风丧胆。“你难道不想给这家报纸的编辑部写封信?”我实在气不过,咻咻地问徐扶明教授。 “这没用。”他说:“老弟,人生如戏,角色早就定了。有人永远是打手,有人永远是挨打。” 他摇头苦笑了一下,又缩起了脖子。猛一看,真像曾远风说的要想掩盖罪行的逃犯。 这很像我爸爸,关押了那么多年,现在平反了,却像是自己理屈,躲躲闪闪地过日子,从来不控诉、不揭发、不声讨。那些慷慨激昂的事,仍然由当年慷慨激昂的人在做。 与徐扶明教授碰面后大约半个月,一天下午,傍晚时分,一个高高大大、鼻子尖尖的老人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他进门就说:“院长,我叫曾远风,有十万火急的事找你!”说着伸出手来要与我握。 我听说是曾远风,心里一咯噔,没有伸手去握,立即回身坐到我的办公椅上,问:“什么事?” 曾远风走到我的办公桌前,神秘地说:“上海在‘文革’初期演过一台戏叫《边疆新苗》,你知道吗?” 我既没有吱声,也没有点头,等他说下去。 “这是‘文革’期间上海最坏的戏,比样板戏还坏。样板戏剥夺了人民看别的戏的权利,《边疆新苗》剥夺了青年上学的权利!”听到这话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要不是想到了徐扶明教授,我还有可能点一下头。 但是,我看他一眼,已经对他有了鼓励,他的声调提高了:“这个月,正是当年上海学生到边疆去二十周年,受害者们已经集中起来,准备找那个姓沙的剧作者算账,要他归还青春。现在这个剧作者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我听说,他已在托人找您,请您出场去说服那些受害者。我今天紧急赶来,就是劝您千万不要为他出面!” 不管曾远风是不是夸大其词,如果一群二十年前去边疆的人员真的包围住了那个剧作者,这可不是小事。大家一激愤,闹出人命都有可能。我便问曾远风:“真有这事?”他就把消息来源详细说了一遍,我听完,就把他打发走了。 我立即把我的好朋友胡伟民导演找来,商量这件事。胡伟民像我岳父一样是个“右派分子”,“文革”中不在上海,不知道有《边疆新苗》这个戏。但他显然看不起那个剧作者,原因说不上。我说:“有那么多人来讨二十年前的旧账,可见那个戏确实很坏。但当时逼迫青年学生下乡,是北京的号令。这个剧作者只是曲意逢迎,现在如果把历史责任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 “这不妥!这不妥!”胡伟民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 两天后,《边疆新苗》的作者果然来找我了。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个人,他的态度,不是我预想的那样忧虑和谦恭,而是一种带有一点滑稽的友好,这使我觉得比较舒服。 第二天傍晚,我就出现在那个现场。是安福路上一个剧场的门厅,我去时已经挤满了人,门外还有不少人要挤进来。一看就知道,全是二十年前上山下乡的学生,社会上统称为知识青年,又简称为“知青”。 《边疆新苗》的作者靠墙坐在一把塑料的折叠椅上, “知青”们都站着,由于后面推挤,对他越逼越近。我怕出事,就站到了他身边。 一看就知道,这些无言的人不是来闹事的。他们最好的年月都被拿走了,但是谁也没有为这件事承担责任,只是草草地让他们回了城。城里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找不到出路,于是像没头苍蝇一样撞到了这里。安福路在上海是一条小路,并不好找,但他们还是找来了。眼前这个坐在塑料折叠椅上的胖乎乎、矮墩墩的男人,显然不是他们真正要找的人,但是,除了他,他们再也找不到别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