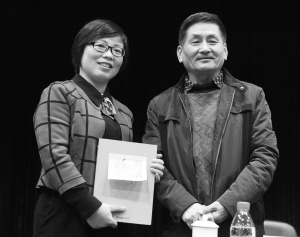 |
| 叶辛向鄞州图书馆赠送新作《圆圆魂》(手稿版)。 |
□记者 陈晓旻 文/摄 作为2000万知青的普通一员,1969年从上海到贵州修文县插队,1979年调回城里,他经历了十年“文革”。作为知青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到今天,他一直在关注和记录着那一代人的命运。他就是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他创作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以及由他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均在国内引起轰动。 4月1日下午,叶辛应邀做客鄞州图书馆“明州大讲堂”开讲《我们曾经年轻》,回忆那曾经的“蹉跎岁月”。花白的头发,低调随和,但说起那些年那些事那些创作和那些体会时,他还是充满了深情。开讲前,他把新作《圆圆魂》(手稿版)赠送给鄞州图书馆。 我的青春落户在贵州山区 叶辛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出生在上海文化广场附近一户普通市民家庭里。叶辛原名叶承熹,儿时的他常到外滩看在黄浦江上穿梭的大小轮船,梦想着当一名水手,驾着轮船驶向大江大洋。后来,他读了许多中外文学名著,又梦想着上大学中文系,成为一个作家。 1969年3月31日,高中刚毕业的叶辛,作为两万多名赴黔上海知青中的一员,从黄浦江边前往云贵高原,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来到贵州省修文县久长镇永兴村砂锅寨插队落户。 农村的艰苦还是超乎他的想象。他回忆说,当时住的是泥墙茅草屋,没有窗户,在墙上凿一个洞、在洞里嵌一块玻璃,就是窗户。男知青还好,女知青生活很不方便,泥墙茅屋容易干裂出一条条的缝,她们只能将报纸塞在缝隙里,再贴一张报纸来阻挡墙面透光。 贵州多的是山地。他每天扛着农具翻山越岭走向山间田野,挖地、耙田、播种、锄草、收割,他还当过放牛郎,每天赶着牛群到山上去。他说喜欢与牛对话、与草木对话、与大山对话的生活,山野让他觉得开阔,也觉得安静。这个时候还可以看书。 “看我常常捧着一本书看,同一知青点的知青问我干什么,我说想读出书的奥秘来。”叶辛说,在看了7遍法国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红与黑》后,他读懂了长篇小说的作品结构。他说要写小说,没想到被大伙儿嘲笑了一番,说你一个中学毕业生怎么写?叶辛说,《红与黑》第一章写小城,坐落在法兰西中部的山上;那我第一章就写我们插队落户的村子,坐落在山沟里,村里有56户人家,我们都很熟。《红与黑》第二章写市长,50多岁,个子高高,他的政治态度等等;我就写村长,每天劳动时他脖子上挂个哨子,吹一声催大家出工,也有很多故事可写。 这第一部小说叫作《春耕》。病休回上海的同学给他寄来方格稿纸,当时同为知青的女朋友(后来成为叶辛的爱人)帮他誊抄了初稿。但是这部花了几年时间写成的40万字的小说手稿寄往出版社后,收到的却是退稿信。 叶辛透露,自己的处女作《高高的苗岭》其实是“无心插柳柳成荫”。1974年,他被上海文艺出版社邀请去修改第二部作品《岩鹰》,住在作者宿舍。一起改稿的作者有好几个,编辑们也会常常过来和大家沟通。一次一位儿童文学编辑问他会不会写儿童文学作品,叶辛就把自己写的《高高的苗岭》给编辑看,没想到编辑认为基础不错,建议加工创作。于是叶辛加上了自己熟悉的苗寨故事,修改了三次后,1977年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后他又出版了《深夜马蹄声》,《岩鹰》则是他第三部出版的小说。 《蹉跎岁月》和《孽债》 对于一个作家,经历是一种财富。对于叶辛,10年的知青生涯是他创作的源泉。 《蹉跎岁月》是叶辛第一部真正产生影响力的知青文学作品,1980年在《收获》杂志发表。那年《收获》杂志发行了110万份,是有史以来印数最多的一期。 叶辛回忆说,这部小说和一个故事有关。1979年他到北京,参加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上大家围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能不能写悲剧”进行了长达一天半的讨论,也没争出个结果来。后来,湖南的一个作家站了出来,讲了个故事,说,你们看看是不是悲剧。 “文革”期间,他到湘西当知青的带队干部,故事就发生在那时。北京来的“黑帮”的儿子,被下放到农村放羊,遇到同样被下放到当地放鸭子的“历史反革命”的女儿。两个年轻人开始相恋,6年来感情非常好。1976年,“黑帮”的儿子因为父亲平反,被调回北京;女孩子的父亲因为是“历史反革命”,无法平反。离开湖南前,男孩子承诺帮女孩子回城相聚,但终究因为她的家庭成分没能兑现诺言,女孩收到男孩来信后投河自杀。 他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全场鸦雀无声。会后,叶辛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今天所说的有关知青的故事,我可以把它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但我要把它的结局写好。这就是《蹉跎岁月》的故事雏形。他说: “上山下乡影响了知青一生的命运,他们在农村的十年岁月是怎么过来的?对他们以后的人生是怎样的改变?我想通过我的小说告诉今天城市里的读者。当时我经常用‘岁月蹉跎志犹存’自勉,所以就用它做了书名。” 1983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由他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引起轰动。那个时候电话没有普及,很多人都是靠书信来表达。“我自己收到的是1700多封来信,中央电视台收到的转给我的信,是用好几个麻袋装的。” 另一部感动人的长篇小说是《孽债》,关注的是知青的下一代,写的是一群来自西双版纳的孩子到上海找父母的故事,他们的父母当年是插队落户云南的上海知青,如今已经有了全新的城市生活,孩子的突如其来迫使每个人对生活开始新的思考。 《孽债》的故事,也和叶辛自己的经历有关。1969年到贵州砂锅寨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一共有60个,后来招工、招生,大家都陆续走了,叶辛是第59个走的。迁户口的时候,民政干事跟他说现在只剩下一个小丁,她嫁给了当地农民,按照知青返城政策,已婚知青不能返城。 当时,叶辛回老乡家里拿行李,离开寨子的时候碰到了小丁,她手里牵着一个五六岁的娃娃,笑嘻嘻地对他说“祝贺你”。看着她肚子又大了,叶辛问她“你怎么办”。谁知听了这话,她整个脸都阴沉下来,说了一句“我也要走的”。叶辛说写《孽债》最初的原因就是这个———如果小丁回上海了,她的孩子们怎么办?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有类似的故事冒出来。一次,他听云南大学的一位老师说了一个故事。这位老师带着学生去西双版纳采风,住在一个招待所里,碰到一个女同志,每天专注地站在大门口。一问才知道,她是北京知青,曾在西双版纳来插队,嫁给了一个傣族汉子。恢复高考后,她考上了北师大,离了婚,独自回北京去了。这次她来西双版纳是来找孩子的,一个乡一个乡找过来,一直找不到,就住到市中心的招待所,指望着每天傍晚人最多的时候,走在街头能碰见孩子或前夫。叶辛说: “在此之前,我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知青故事,但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我决定要写了。小说名字就叫《孽债》。1995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播出后,再次创下了收视率之最。” 换一种目光回看知青岁月 《客过亭》是叶辛近年的作品,由作家出版社2010年出版。这个长篇小说写的是知识青年步入晚年时的一些往事和故事。2014年,他又创作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问世间情》,同为知青题材,但是这次他把对人的关注和对现实生活的关注结合了起来,以往的故事关注悲欢离合,而这部作品更多是关于人命运的思考。虽然知青还是主角,但是叶辛将关注的眼光投向当下“新上海人”中的底层劳动者,关注农民工进城后的情感生活,探讨了改革开放和城镇化浪潮中不可避免的情感变迁和生活矛盾。 为什么要坚持知青题材?叶辛感慨地说:“我下乡时间和一般人相比要长,我对知青们的思想演变过程等种种细节都了解得非常清楚,感受就特别深。插队生活使我学会了用两副目光来观察生活,回看知青岁月,经常会给我创作上的灵感。” 199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了《叶辛经典知青作品文集》8卷本,题记是:“一代人的青春,是知青们用汗水和眼泪、苦涩和艰辛、希冀和憧憬,在蹉跎岁月里写的。” 叶辛的创作非常有规律,他不喜欢晚上熬夜创作,通常只白天写作。因为构思小说,常需要冥思苦想,会影响睡眠质量。每天的散步和练书法是他的养生方法。 上个月,“叶辛文学馆”落户于浦东新区书院镇的一个老民居中。知青岁月让叶辛对乡村有一种情结。在叶辛看来,乡愁是一种人文情怀,是人们对土地、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的情感,文学表达、文化元素是“乡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他欣然应允在书院镇建立“叶辛文学馆”的原因。他说,好作品能让社会变得温暖,文学始终是人可以安放心灵乡愁的“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