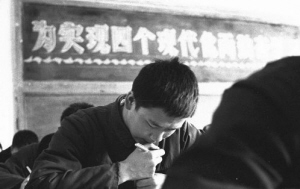 |
| 资料图 |
 |
| 1977年的准考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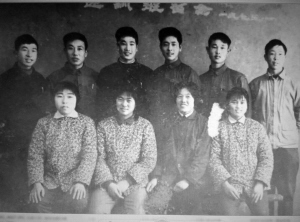 |
合照右上二为沈志久。
记者 徐叶 翻拍 |
□记者 李臻 徐叶 童程红 通讯员 袁红丽 沙颖莹 又到一年高考季。那一年,我们或许都曾经历过高考,是让你热血沸腾还是唏嘘感慨? 自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再也没有一场考试比高考更能影响命运的了。 对上世纪70、80年代的高考生而言,能否考上大学与将来“穿草鞋”还是“穿皮鞋”划等号;至于上世纪90年代的高考生,在市场大潮冲击下,高考对个人命运的影响更加多元化,伴随的是大学收费和自主择业;如今,高考已经从能否上大学的竞争变成能否考上名校的竞争,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选择了出国留学。 高考见证着社会变迁,也在一代代人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不一样的年代,不一样的故事。昨日,记者采访了几位高考时间轴上不同年代的考生,听听他们的高考人生。 1978年 高考,与父亲吵架吵来的机会 沈志久的老家在北仑区东南部的梅山岛,如果徒步“丈量”,他家距离当时的郭巨镇郭巨中学足有单趟两个多小时的脚程。 1975年高中毕业,沈志久17岁。劳动一年后,在家乡当起了“赤脚医生”,即便不再上学,他也从未放弃过自学。除了医学知识,他还到郭巨镇上买到了一本《高等数学》,潜心自习。 1977年的一天,郭巨中学教师金龙土上门给他送去了一个好消息:高考制度回恢复,又能考大学了。 “有个大学梦想,就没考虑过大专。”沈志久昨日在接受采访时说,除了感恩好的教育政策,还特别感谢当时的金老师,因为他挨家挨户通知,上门做动员工作,足迹遍布了郭巨、峙头和梅山。很多同学的命运就因为他热心传达的信息而改变。 当时,沈志久是家中主要劳动力,“赤脚医生”收入也不错,得知他要去参加高考,父亲是强烈反对。为此,沈志久与最敬重的父亲吵了架,最后父亲拗不过他,默认了。之后的日子,他每天来回走30公里,就为到学校听老师上辅导课。 那年高考试题,沈志久至今记忆犹新,“首届高考分初试和复试,一共有五门:数学语文化学物理和政治。当年的语文作文题,《十月》和《路》。” 1978年2月,沈志久收到了温州医学院的入学通知书。当时恰逢哥哥喜得闺女,他就给侄女起了个小名叫“双喜”,分出去的喜糖足有20多元。当年的郭巨中学,大约有60多名学生备考,也因为首届一下子考上30多个学生而名噪一时。要知道当年,高考录入率仅为3%至4%。 “可能是想把虚度的时间补回来,很多同学上大学后很拼命,那些大我们十岁的‘老大哥’们尤其刻苦,说是废寝忘食真不为过。”沈志久说,那种勤奋和珍惜如同信仰,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理解。 现在,沈志久已是宁波市第一医院肾病泌尿中心主任医师。在沈志久看来,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改变了个人的命运,也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当今的社会。对“沈志久”们而言,高考无疑是人生最重要的转折,可能没有之一。 1992年 2颗白色药片让她终于安睡 42岁的徐智琴,1992年参加高考,现在是上海一家证券公司的高管,在那座大都市里也是典型的金领。 “我的高考考场在鄞州中学,当时还叫鄞县中学。”徐智琴当时她读的是文科,那时高考时间还是在7月的7、8、9三天。她的记忆里,高考伴随着炎热的天气,操场上知了没完没了地叫唤,还有考场里那几箱为考生降温的冰块。 哪怕过了20多年,考前那个晚上的煎熬总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很小的细节也记得一清二楚。 徐智琴说:“高考前一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太焦虑了。那时我们是12个人的大寝室,我已经听到有同学呼噜声了,心里就更急。后来老师巡查到我们那儿,给我一个白色药片,说是有助于睡眠的。可是吃了后我还是睡不着,辗转反侧,没办法只好又出去找老师要药片。那时估计已经是下半夜了,吃了后就迷迷糊糊睡到了天亮。” 高考那三天,徐智琴一直处在兴奋中,而到了最后一天人已经极度疲倦,考完回寝室后倒在床上,整个人就虚脱了。后来,老师告诉她,其实那几天班里很多同学都没睡好,他给大家吃的白色药片说是有利于睡眠,其实只是维生素,“心理上安慰下大家”。 当时这么在意高考,因为对于当时的农家孩子来说,这场考试决定着自己将来的命运。如果考上大学了,那就是跳出“农门”,从此跳进了“龙门”。徐智琴说:“龙门和农门,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区别却是非常大。那段时间我们老师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一定要发奋图强,跳进龙门!” 那时候,是考完先估分再填志愿,徐女士考出了高出重点线30多分的分数,却没填好志愿,最后被上海金融专科学校录取了。工作后的她一直在进修学习,工作又踏实勤奋,从基层一步步做起,经过20年的努力也小有成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