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陈玉青。记者 滕华 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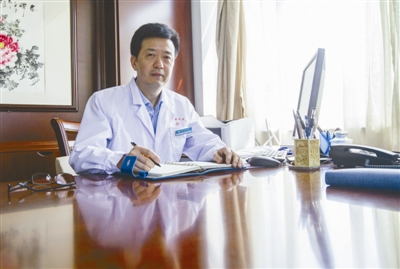 |
| 余晶波。记者 刘波 摄 |
 |
| 王雪芬。记者 刘波 摄 |
 |
| 李军。受访者供图 |
“指导员”陈玉青: “杂牌军”率先完成任务 制作纪念册留住青春岁月 人物简介:筑路那年,陈玉青29岁,是江北区团委负责人,任“共产主义筑路突击营”三连指导员。2010年从江北区妇联主席岗位退休,如今是一名志愿者。 1984年2月25日早上,陈玉青所在的连队进驻工地,他们主要负责宝幢段的路基工程。来自17个系统单位的145名青年,坐在10多辆军车上,浩浩荡荡一路向东。 “别人都开玩笑说我们是杂牌军,人员太散太杂。”陈玉青说,145人中,只有16个女性,而且普遍年龄都较小。作为指导员,陈玉青体贴地把她们都分配到了各班任副班长。 “杂牌军”也有“杂牌军”的优势,陈玉青就发掘了不少身怀一技之长的能人。比如,来自宁波动力机厂的面点师傅,被分配到了食堂,每天早上,三连的馒头飘香,总能引得别的连队暗暗羡慕。 陈玉青说,当时筑路突击营常驻人员1000多号人分散住宿,有的租住农民房,有的住在生产队的牛棚里,他们三连算是条件不错的,住在阿育王寺的附属房里。每天早上6点不到,大家就起床了,山里冷,毛巾都冻成了冰条,由于炊事班来不及烧热水,他们只得用结冰的水洗脸。 突击营需要在五十年代荒芜的旧路基上“再加工”,但这些旧的路基不仅荆棘丛生、杂草遍地,更面临土质不宜施工等问题。大家只得到育王岭附近的凤凰山上搬运泥土,缺少机械工具,队员们便用肩挑,用手推车推拉。土方推到路基上,再用“青蛙式”打夯机打实。4个人抬起一个木头,跟着“嘿呦嘿呦”的号子声,一下一下夯实着路基。 “当时整个工地都是建功立业的氛围,身边每个人都是这样拼命地在干。”陈玉青说,她深刻地感受到,这項工程就像熔炉,很多年轻人变得不一样了。 让陈玉青骄傲的是,1984年3月23日,“杂牌军”在几个连队中率先完成工程任务凯旋。三连的青年们也在筑路劳动中交下了一生不忘的朋友,临分别时,连那些平时沉默坚毅的汉子都哭了,泪花中有激动又满是不舍。 为了记下这段珍贵的岁月,陈玉青策划制作了一本共青团北仑铁路筑路突击营第三连的纪念册,里面记载了每一位队员的名字、性别、文化程度、所在单位、家庭地址、特长。册子有些发黄,翻看这一页一页的名录,34年前他们每一张年轻鲜活的笑脸仿佛就在眼前。 “独苗”卫生员余晶波: 一人“掌管”两三百战友健康 至今存有100多位突击队员电话 人物简介:余晶波,男,生于1962年,现任宁波市第一医院副院长,时任宁波市第一医院团总支委员兼内科团支部书记。 余晶波提起当年的“共产主义筑路突击营”,语气中充满自豪:“我们突击营只有优秀的团员青年才能参加,一般团员想上也上不了。”时隔34年,余晶波仍是一口一个“我们突击营”,仿佛那些岁月并没有走远。 由宁波市优秀团员青年组成的“共产主义筑路突击营”成立于1983下半年的秋天,为修建宁波到北仑港的铁路路基。当时的余晶波才22岁,工作不到两年,他是市一院团总支委员,团总支委里一共7名委员,5名女同志,2名男同志,“听说那里条件比较差,女同志不合适,另一名男同志妻子刚生小孩脱不开身,只剩我了。”余晶波说,当时还是很“庆幸”,没人争没人抢,自己能顺利加入突击营一连,也就是“先锋连”,成为一连的卫生员。 怀着一腔豪情来到现场,余晶波发现这里的条件何止“比较差”。“没有自来水,只能抽河水上来,烧水做饭用的是河水,洗脸刷牙用的也是河水。我们连所在地明伦村全村只有一部公用电话,路况也很差,基本上大家都是‘通讯靠吼,交通靠走’。” 刚开始的两个多月里,全连乃至全营卫生员只有余晶波一人,由于其他连里没有卫生员,有时要负责几个连两三百号人的健康。每天6点左右要起来,夜里11点多才躺下,半夜被叫醒去处理突发状况也是常有的事。最惊险的一次,有人半夜突发快速型心律失常,经余晶波紧急处理后,连夜把他送到宁波第一医院住院。 直到次年4月,突击营完成任务,宣告解散。但成员间的情谊就此结下了。“那几个月里,大家同吃同住,夜里也经常在一起聊天。人来自各行各业,话题也是海阔天空,具体聊什么现在想不起来了,但那种开心又新奇的感觉还是记得的。”余晶波告诉记者,至今,自己的手机里还存有上百名突击营成员的电话,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还是经常联系,有时也会聚在一起话当年。 “后勤总管”王雪芬: 惭愧第一顿饭煮夹生了 咸菜肉丝包给战友们当“下午茶” 人物简介:王雪芬,女,生于1959年,现任宁波市公安局技侦支队副调研员,时任市粮食局专职团委副书记、团市委委员。 “那时候大家都那么年轻,充满激情。”回想起34年前参加共产主义筑路突击营的时光,年近六旬的王雪芬眉飞色舞,对她来说,那段日子弥足珍贵,日记、照片她都保存至今。 王雪芬当时是三连的副连长,分管全连100多人的饮食起居。1984年大年初四,她带着十几名团员,赶在大部队之前来到了驻地——育王寺。 忙活了一周,粮油米面到位了,各式炊具到位了。寺庙里师傅们不吃肉不杀生,但筑路青年们干了一天的粗活重活,饭菜里总得有点鱼肉荤腥,不然体力跟不上。为此,王雪芬找到方丈,希望方丈能够通融。方丈同意了,但也提出一个要求,不能用寺里的厨房烧荤菜。于是,大家又一顿忙活,搭起了临时厨房。 万事具备,大部队也来了,第一顿饭却是夹生饭。“当时,我惭愧得不行,眼泪都快下来了。”王雪芬说,大家没有意见,夹生饭也吃得开心,但她和炊事班的成员却连开了两场紧急会议,分析原因,以后该怎么避免,“比起其他在一线挥汗如雨的团员青年,后勤工作要轻松得多,再不做好就太说不过去了。” 但事实上,所谓轻松的后勤工作一点也不轻松。有的女同志,要清早四五点钟穿过一片墓地去给大家买油条;有的男同志,夜深了还在给大家修理铲子等劳动工具。而炊事班的成员,天天给大家做饭,自己却往往是最后才吃上饭。 怕大家下午劳动到一半会饿,王雪芬就给大家做“下午茶”。“那时候条件差,‘下午茶’也就是咸菜肉丝包和茶水。”做好后她和另一名女同志一起抬到工地,虽说离得不远,但老式茶桶少说也有30多公斤,两人也累得够呛。 1984年3月底,三连任务完成。当晚,大家聚在一起,喝了庆功酒,吃了一顿有鱼有肉的“大菜”,“吃完还不尽兴,大家心里攒着一股高兴劲儿,一群人手拉手,边走边唱,边走边笑,一直从育王走到大碶,从天黑走到天亮。”王雪芬说,现在想起来,多么傻气又多么可爱。 “采购员”李军: 最怀念不分你我的战友情谊 突击营里认识了后来的妻子 人物简介:李军,男,生于1959年,现任宁波市炊事机械厨房用具有限公司职员,时任宁波市土产日杂有限公司保卫科干事。 时隔34年,想起当时共产主义筑路突击营里,人与人之间不分高下不分你我的情谊,李军还是很动容。 1983年,李军被借调到市检察院。原单位一个电话把他叫了回来,于是他成为共产主义筑路突击营三连的一名采购员。这是个重要的任务,交给李军是因为他在部队有过帮厨经验,又早早入了党,是团员青年们非常信赖和喜爱的“大哥”。 “前一天晚上,厨师长把菜单交给我,第一天一早,我和司机开着一辆小货车到灵桥路的大世界菜场去买菜。每人每天几毛线的伙食标准,我们都想着法子给大家换换口味,增加营养,怎么也得保证两菜一汤。”李军说。 由于采购量大,加上路况不好,采购员的工作很辛苦。清明四五点钟,多数人还在睡的时候,李军就起床了,揉揉睡眼便上了车。赶到菜场,又当起搬运工,肉、菜、蛋,一买就是几十公斤,扛上扛下,大冬天也能出一身汗。 “当时大家都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心就想把路修好。”李军说,比如,进城去拿粮油采购卡的同志即使到了饭点也要赶回来,说是集体的饭香,其实是想多干点活;干部说是干部,但没有人端出干部的架子,有困难都是自己先上,热菜热饭都是让一线筑路青年先吃。 李军后来和当时同在三连的一名姓孙的女同志喜结连理。有人打趣说,这是在突击营几个月结下的情缘,人家修路,他修出个老婆。对此,李军连连否认:“没有的事,当时大家都忙得脚不沾地的,也就见面打声招呼。”但这段情缘也和突击营有关。原来,任务完成后,大家组团去黄山游玩,一路上,李军和这名女同志热络起来,后来又发现双方住得很近,走动就更勤了,最后才成就了好事。 共产主义筑路突击营已经过去了整整34年,李军也不再年轻,但那段青春飞扬、激情澎湃的日子仍然深藏心底,偶尔重温,嘴角便泛起笑意。 记者 滕华 童程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