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大运河摄影工作坊摄影师李柏丰、丁若姮、张立能、余锡芬、吴铭铭拍摄制作的名为”出发“的长卷(局部)。 |
 |
| 2022年的三江口。 沈颖俊 摄 |
 |
| 20世纪80年代的三江口。戚颢 摄 |
 |
| 桂月红2019年在淮海路。戚颢 摄 |
 |
| 2022年8月拍摄的通济桥。 沈颖俊 摄 |
 |
| 1987年11月拍摄的余姚通济桥。 戚颢 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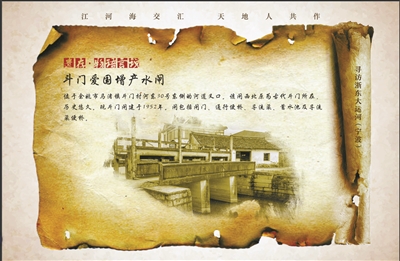 |
| 马渚斗门爱国增产水闸。 邱文雄拍摄制作 |
 |
| 2022年的宁波外滩。沈颖俊 摄 |
 |
| 20世纪90年代的宁波轮船码头。 戚颢 摄 |
去年年初起,宁波市摄影家协会大运河(宁波段)工作坊的近30位摄影师沿着河寻找、记录、拍摄,历时一年多,用数万张照片定格她最真实的样子。 本报与宁波市摄影家协会、新甬派拍客频道联手推出栏目“寻脉大运河”,陆续呈现你我都有共鸣的运河故事。 公元821年,明州州治移至三江口,并筑子城。 这件在史籍中记载寥寥的“小事”,像一只蝴蝶在那年的明州轻拍了一下翅膀。天下港城,由此发端。 从此明州站在了大运河南端出海口和海上丝绸之路东方始发港的交汇处,一代代人从这里东出大洋,西联江淮,转运南北。港通天下,将中国与世界相连。 这个宁波普通家族最早的出发,就从三江交汇奔流入海的地方开始—— 三江口 1984年来宁波前,桂月红从没想过,漂泊多年之后,自己会把家安在三江口。 这是她小时候听爷爷、大姑和爸爸描述过无数次的三江口,是他们家和很多同乡去上海谋生的出发地、无数人命运的转折点。 桂家的银楼曾在镇海盛极一时。只是后来爷爷每一次说起金银首饰和其所代表的富贵荣华时都被大姑打断。大姑总是强调财富都是过眼云烟,不要放在心上。可能对这位含着银钥匙出生的桂家长女来说,当年变故过于刻骨铭心——一场大火烧掉祖业,爷爷和母亲相继离世,父亲撑不起家业,所幸丈夫在上海大新百货、也就是后来上海第一百货的前身谋得职位,才把这个遭受重创的家带到上海重新开始。 也这是上海移民史的一个缩影,早在20世纪初,上海坊间已有“无宁不成市”的传统。极富商业头脑的宁波人,组成了沪上毋庸置疑的第一商帮。他们不仅精于生意,而且注重乡情,往往一个人在上海立足,会将整个家族的人都带来。桂月红当时只有10多岁的父亲,也是在姐夫的引荐下,在药材公司谋了份差,辛苦多年后站稳脚跟,娶了外滩一银行职员的女儿,也就是桂月红的母亲。 桂月红的外公是余姚临山镇湖堤村人,也是十多岁到上海打拼,在外滩银行找到稳定工作后,把家安在旁边的董家渡。 1952年,桂月红出生后,这个移居上海多年的大家庭境况渐好,长辈们常常说起宁波,说起三江口。以至于1984年,几经波折的她终于把家搬到这里时,有片刻恍惚,这个地方,好像在梦里来过了很多遍。 她家对面就是轮船码头,当时上海客运公司有8艘船轮流往返宁波、温州、福州,“繁荣昌盛,茂鸿展望”,8个字后面各加一个“新”字,就是船名。隔江一声长鸣,总让人心旌摇动,仿佛半个世纪前,大姑带着爷爷父亲离家时的那艘船从时光隧道驶来。 淮海路 父母生了6个孩子,桂月红是第一个女儿,从小到大新衣服最多。每一次,都是姆妈从“宝大祥”挑了布,带她到熟悉的裁缝铺找宁波来的师傅做。 两代人的辛苦打拼后,桂月红的家,从延安路瑞金路路口,搬到了西藏南路淮海路路口,又搬到了淮海中路115号,都是老上海人心目中的“上只角”。 商业的繁荣和从小的视野相辅相成,即便桂月红的家很小,小到煤气炉只能放过道,经过时都要侧着身,但打开窗就豁然开朗,能看到松软的白云从法国梧桐的顶上悠悠飘过,下面有轨电车叮叮当当来来往往。每每有重要人物来,都会住旁边的锦江饭店,夹道欢迎的队伍就在窗前排开…… 小时候以为上海就是全世界,后来见识了更大的世界,上海倒成了回不去的家。 户口本上有桂月红名字的那一页,敲着一个红红的章“迁出”,是17岁去插队那年敲上的。 那是她人生第一次出发,从上海北站,成千上万的知青在那里惜别家人,离开繁华城市去山野农村,命运从此拐了个弯。 桂月红要去的地方是余姚临山镇东的湖堤村,那是母亲的娘家。父母觉得,横竖要去,不如找一个有亲戚照应的地方。时代的波涛汹涌不可阻挡,故乡,是人们面对变故时最先想到的庇护所。 通济桥 只身离乡的上海小囡果然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第二年桂月红就进了村办服装厂,不用再下地,之后被派去学习两年,回来当了初中数学老师。 丈夫是村里为数不多的高中生,出生于余姚一个读书人家,结婚后带她去城区的古建筑舜江楼玩。桥下姚江是大运河余姚段主体部分,是过去转运经济汇集的中心、官船自京城去宁波的必经之路。江上的通济桥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姚江上最高最长的桥,当年王安石曾在这里留下诗:“山如碧波翻江去,水似青天照月明。”这座桥据说始建于北宋年间,这么多年建了毁,毁了建,经历了岁月的洗礼,见证着舟楫往来带动百业兴旺。 1977年,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时,桂月红虽然知道这是改变命运难得的机会,也自信有试一试的实力,但还是决定守着年幼的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女儿,全力支持丈夫去考试。 马渚 1978年秋天,桂月红带着一双儿女,坐着汽油船到马渚镇的火车站,送别去湖南上大学的丈夫。 马渚,是虞舜运河的终点,南宋起便有陡门、闸坝等设施的记载。不同年代建造的老闸新闸,助力船来船往,把人和货物送向更远的地方。 终于等到1982年丈夫毕业,他分到了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研究院,在杭州。但因为种种原因,桂月红的户口却迟迟不能迁过去。1984年,儿子读初中了,当地的教育质量让桂月红开始夜夜辗转反侧。自己可以随遇而安,可孩子不能耽搁。 思来想去,后来用了个折中的办法——把儿子转学到余姚城里,寄养在亲威家,那里教育质量更好些。 一周后,儿子给她写了一封信,没说不习惯,只说想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桂月红看得眼泪掉下来。她去余姚把儿子接到身边,然后联系丈夫:“你给我回来!无论如何,一家人要在一起。” 所幸这一年,宁波市政府去杭州招聘人才,丈夫选择调到宁波。这座素来重视人才的城市不但解决了一家四口的户口问题,还给他们分了当时十分紧俏的三居室套房。 终于团聚起来的小家庭,把家安在了三江口庆安会馆附近的史家新村。虽然那时旁边的江厦桥还只是一座浮桥,市中心很少有像样的高楼,但心怀感激的他们决定一心一意为这座城市添砖加瓦。 外滩 上海知青子女返沪工作落实后,桂月红的两个孩子有一个可以回到上海。这时儿子已经工作,这个名额顺理成章地给了13岁的女儿。 下一代要出发了,桂月红像当初母亲送自己插队一样,把女儿送到了轮船码头,心里百感交集。 当年敲着“迁出”章的户口本上,多年后“迁入”的姑娘和母亲有着相似的眉眼和脾气,她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大学毕业时浦东开发热火朝天,当地求才若渴,余姚乡下长大的外地姑娘很快在国际化大都市站稳了脚。桂月红也更确定,孩子就应该出去闯闯。 许多年后,她又和儿子一家一起,去上海浦东机场,送孙子去英国读研究生。 那时老外滩客运码头已经不在,杭州湾跨海大桥和高铁缩短了两座城市的距离。一代又一代,牵肠挂肚地目送。桥路生长,航线延伸,世界越来越小,孩子们的天地越来越宽。 桂月红错过了好几次回上海的机会,但回过头来看,她不后悔走过的每一步。宁波这座不断成长的城市,给了她从头开始的机会,最后在一家事业单位科长位置上退休。 两年后,孙子回国,进了上海一家银行。他带着桂月红去自己工作的陆家嘴,对面就是外滩:“奶奶,爸爸说你的外公当年就在外滩的银行上班?” 时光就像人生舞台悄然切换的幕布,一恍惚一出神间,斗转星移。 桂月红的人生连接了两种风景,一头是爷爷、外公那一代移民口中的旧社会“十里洋场”,另一头是自己的孙子,新一代海归见证并参与的新时代经济腾飞。中间的漫长光阴,走得很辛苦,每一次选择和取舍,每一次回归和出发,都在积攒力量,孕育希望。 时间无情,但一代代人的生命轨迹会超越时间彼此呼应。冥冥之中,命运在奇妙地延续,一代宁波人将接力棒交到了新一代宁波人的手里。 他们再一次出发。 记者 樊卓婧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