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北京通惠河玉河遗址。(记者 周建平 摄) |
 |
| 4月29日,北京市通州区燃灯佛舍利塔景区,记者在采访骑游大运河的申遗志愿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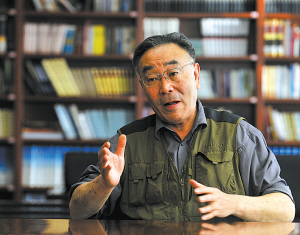 |
| 4月28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专家赵福生接受记者采访。 |
宁波—北京 大运河南北端城市历史文化的呼应 2500多个春秋冬夏,中国大运河日夜不停息地奔流着。数千公里的跨越,把大运河最北端城市北京和最南端宁波两座城市紧紧相连,最终从东海之滨宁波奔流入海。 曾经,客运、商运、漕运,茶叶、丝绸、瓷器和粮食等物资千里迢迢地从宁波通过大运河北上来到京城,为帝国的绵延注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 然而,大运河何止是一个贯通南北的运输通道?它连接的是历史,呼应的是文化。 大运河是政治变幻的透视者。 浙东学术的代表人物、一代心学大师王阳明,著名藏书家范钦,曾舟渡曹娥江、钱塘江,沿着浙东运河北上京城,在这里见证了16世纪灰暗的政治天空。 1482年,11岁的王阳明旅居在考中状元任职京师的父亲处,对京城有了最初的印象。当26岁的他再次回到北京,从担任刑部主事到成为兵部武库司科员,初尝了官职生涯的酸甜苦辣。他想不到的是,正德元年(1506年),35岁的他“上书”为忠臣蒋钦辩,触怒皇上,被痛打40大板并投入大狱,后被流放至贵州龙场的偏远驿站。 26年后的嘉靖十一年(1532年),同为宁波人的范钦赴京赶考中进士,与京城有了不解之缘。嘉靖十五年(1536年),就在什刹海旁一墙之隔的紫禁城,升为工部员外郎的范钦成为管理紫禁城内外宫殿、庙宇和皇陵建造的官员。在这里,恪守职责的范钦举报武定侯郭勋的贪污腐败行为,被廷杖、蒙冤入狱。一年后的嘉靖十九年(1540年)才被皇帝“开恩”下旨释放。次年,郭勋罪行彻底败露,投入监狱。正义得到了伸张,刚直不阿的范钦以“抗武定侯者”闻名于朝廷。 大运河是历史风云激荡的见证者。 处于“落日的辉煌”的大清帝国与近代西方文明初次碰撞,就是在古老的大运河上发生的。 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向中国派遣了一个有5艘船只,包括军官、传教士、商人、翻译等在内700人的“史上最大来华使团”,表面上是为乾隆皇帝祝寿,实则是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欲同清政府谈判扩大贸易往来。 1793年10月7日,经乾隆皇帝特许,使团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运河之旅:从北京出发、沿着运河南下,抵达杭州。 可悲的是,漠视外部世界变化的大清帝国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称英国人为纳贡朝圣的“番邦”。而精明的“番邦”却在逍遥的运河之旅中,把清朝京城及外地城市中从八旗驻防部队到各地绿营兵外强中干的防卫情况窥探了个清楚。 47年之后的1840年,当年使团中只有12岁的侍童乔治·托马斯·斯当东,在英国下议院极力鼓动进攻中国,鸦片战争爆发,一段残酷的历史由此拉开帷幕。宁波则成为中国被坚船利炮打开大门后,首批对外通商的城市之一。 大运河是文化薪火相传的传播者。 沿着运河流淌的方向,文化精神、学术思想在一次次升帆远行中传播海内外。 王阳明说“人皆可以为圣人”,还倡导“致良知、知行合一”,其振聋发聩的思想照亮了16世纪沉闷而黯淡的政治天空,直接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 京城的历练,锻造了范钦的铮铮铁骨,也让具有极高史料和文物价值的明嘉靖刻本《奏进郭勋招供》成为国内外孤本,珍藏于天一阁,并缔造了天一阁这座亚洲最古老的中国私家藏书楼。 还有在京城19年的清初宁波籍史学家万斯同,他不署衔、不受俸,以布衣参与编修《明史》,写成五百卷《明史稿》,其严谨的修史态度成为史学家楷模。 而今,斯人已逝,运河水依旧无声流淌,悠长的文脉就在历史长河中一代代悄然传承。 大运河是城市兴衰的旁观者。 明弘治元年(1488年),朝鲜官员崔溥在海上出差遇难,从济州岛漂至台州,上岸后由官府接待,经宁波沿浙东运河北上京城,北返归国。在他用流畅的汉文、以日记体记叙这段经历的《漂海录》中,浙东运河“江之两岸,市肆、舸舰纷集如云”,京杭运河的航运和沿岸城镇的繁华足以令今人骄傲。 清末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在宁波、上海、北京生活60多年,大运河沿岸的杭州、绍兴等城市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宁波,从1850年开始的10年间,他学会了宁波话。在北京,丁韪良翻译出版了《万国公法》,首次为中国引进国际法。1898年至1900年,他担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为中国引入新文化、新科学作出贡献。丁韪良在北京写的回忆录《花甲记忆》描述了他心目中的宁波,“在这里找到了毕生的友谊,花了很长时间学习中国知识,也写出了一些最好的作品”,宁波“是一个我毫不夸张地说‘尽管你缺点很多,但我爱你始终不渝’的城市”。 大运河就是一部流动的厚重史书,它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诉说,有太多的人事能够追忆,有太多的思考需要沉淀,也有太多的梦想值得追求。(陈朝霞)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岁月无声,河水悠悠。连续三天细探中国大运河最北端的北京城,走过积水潭、汇通祠、南新仓、大通桥遗址、高碑店闸、通州燃灯佛舍利塔……一条串起千年前中国大运河源头从积水潭到通州的漕运“高速路”展现在眼前,历史深处大运河帆影点点、商贾云集的场景呼之欲出,中国水利令人骄傲的智慧结晶展露无遗。 历史辉煌 中国古代水利的骄傲 对于中国大运河北京段,中国大运河申遗专家组成员赵福生认为,“这是中国古代的水利杰作。元代科学家郭守敬发现白浮泉并主持开凿了通惠河,全线贯通了京杭运河,这是运河工程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中国大运河北京段和郭守敬的名字紧密相连。元至元30年(1293年)秋,担任都水监的郭守敬引昌平白浮泉及西山诸泉水为源,凿成通惠河,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这成为中国元代解决南北交通、人力改造大自然的创举,这是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一件事。”赵福生说,“从宁波等南方城市运来的漕粮到天津后,必须走北运河才能顺利运抵皇宫,但从通州到积水潭20多公里的路途有20多米落差,为了保证水路畅通,郭守敬在这段运河的坝河上修了7个大坝,在通惠河上建了11处24道闸。漕粮等物质在翻越了7道闸口、通过20多个闸口之后,才能到达元大都。在距今近千年前的古代,中国水利已达到如此先进的水平,怎不令人自豪!” 赵福生介绍,元代时,漕运的终点在什刹海,当时这里“野旷千帆集,城穿一水流”,从数千公里外来的漕船可以经过通惠河,直达什刹海旁的积水潭,密密麻麻地遮蔽了“海面”,出现“舳舻蔽水”的壮观景象。而到了明朝,城中通惠河一段已圈入皇城,漕运船不能进城,通州便成为大运河的终点。于是,取“通漕天下、漕运通济”之意的通州便成为盛极一时的皇家码头,清康乾年间平均每年有上万艘漕运船抵达这里,形成“万舟骈集”的通州八景之一。 古今辉映 都市中靓丽的风景线 运河的建成,不仅让古代帝国生命线的漕运畅通无阻,沿岸遗存的码头、水坝、闸口、桥梁、仓库、庙宇、民宅等也成为如今运河上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 在被称为北京城内一串“明珠”的什刹海风景区,前海、后海和西海连成一片,直抵大运河终点积水潭,闸口、码头、故道、遗址等静立其中,成为现代都市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前海的万宁桥上,元朝修建的澄清闸还在,岸边六尊明清两代的石雕镇水兽栩栩如生,市民遛鸟垂钓怡然自得。而在西海的积水潭,水面平静如镜,郭守敬雕像面水而立,注视着当年曾经万舟齐至、忙碌喧嚣的码头。岸边,纪念郭守敬的汇通祠立于一旁,儿童嬉闹、老人下棋,一片岁月静好的场景。与什刹海一路之隔的运河通惠河玉河故道毗邻北京老胡同,胡同内老人倚着旧墙门,聊天下棋搓麻将,游客坐着三轮车,东看西瞧细品味,各得其所。 当年为储藏漕粮的仓库南新仓、北新仓、禄米仓、海运仓等则分布在城内朝阳门、建国门一带,因元代运河漕粮存储而得名的街道名字如仓夹道、海运仓胡同、白米斜街等,保存至今。 依运河而生、依运河而兴的通州城内,虽然当年的盛景已不复存在,但是与运河相关的遗迹依旧留存,如高碑店村的平津闸,作为京杭运河北方段现存最完整的一座石闸,保存完好;挂有2248个铜铃铛、有1400多年历史的燃灯佛舍利塔屹立在运河畔,这座为南来北往的漕船指路、保平安的大运河北端标志“巍巍古塔镇潞陵”,而今已成为通州八景之一;在大运河森林公园内,运河平阔如镜,绿杨花树如画,皇木沉船如烟,吸引着很多游客。 如今北京段运河质朴而又亲和,古老与时尚同在,令人流连忘返。 寻常人家 渐行渐近的运河生活 大运河的繁华早已散尽,它曾经的光芒和生命的张力渐行渐远,但大运河的影响却并没有远去,相反,它正日益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中。全线走过中国大运河的赵福生感慨,大运河申遗之前,很多河段或干涸断流,或又脏又臭,“如今你再去看看,这些河段碧波荡漾、爽心悦目,环境得到很好地改善,沿岸的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在高碑店村通惠河平津闸口旁,69岁的张金奎坐在藤椅上休息,祖祖辈辈生活在运河旁的他告诉记者,他记忆中的运河热闹,茶馆、住家紧挨着运河,“小时候河水清澈见底,我和小伙伴就在河里游泳、钓鱼”,他深情地回忆,“如今闸口环境不错,成了纪念景点,但没有了往日的热闹。现在运河申遗了,我希望它依旧是儿时的运河,乡里乡亲和运河相伴而生,真实亲切。” 最能感受到运河两岸百姓安居乐业的要数64岁的于贵海和66岁的裴兴权了,这两位来自吉林省吉林市的中国大运河申遗志愿者,4月2日从中国大运河最南端宁波出发,骑行2500公里,昨天到达中国大运河最北端通州。记者在通州燃灯佛舍利塔下邂逅了两位老人,于贵海告诉记者,一路上骑行在大运河旁的公路上,常常一边是运河、一边是公路,路上车不多,风景优美,令人心旷神怡。“大运河运输缓解了陆路交通的压力,尤其是船运物质多是煤炭、石灰、水泥等,减少了空气污染、经济成本也降低了。”于贵海深有感触,“对于大运河申遗,从宁波到北京,百姓都非常热情地予以支持。大运河申遗将进一步促使南北水路交通的便利,低碳环保的交通也给两岸百姓带来了生活便利,人民生活将更加幸福美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