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雷默部分小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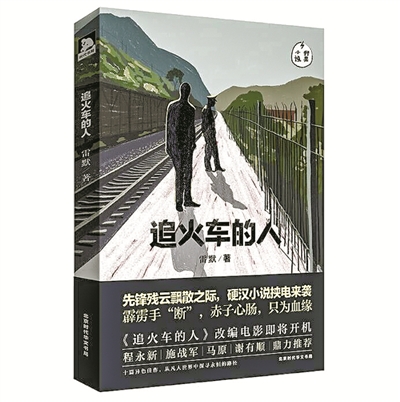 |
| 雷默部分小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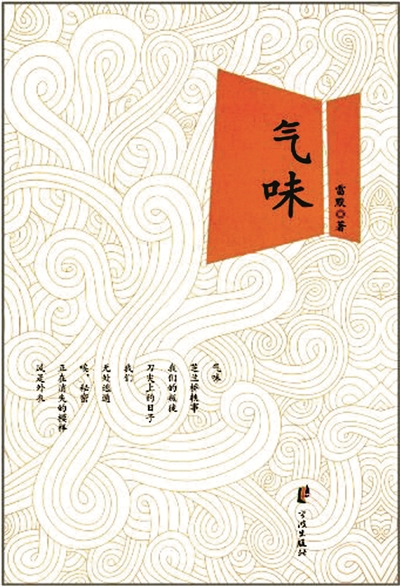 |
| 雷默部分小说 |
李德南 问:首先祝贺你获得第四届茅盾新人奖,很高兴能一起谈谈写作的话题。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你倾向于选择哪篇作品作为个人写作的起点?我指的是,你的哪篇作品意味着个人写作的真正的开端。 答:有意识的创作始于2005年,那时候,我已经工作,在一个小县城的电视台,整个县城除了工作上的同伙,没有一个熟人,房子是租来的,除了上班就是回出租屋休息,出租屋在一个老小区,一个楼梯上去有三户人家,我租的是楼梯拐角的夹缝间,照理那应该是堵墙,可是开了一道门,推门进去,里面都是旧家具,还有一台十四寸的彩色电视机,那台电视机有一天我看着看着,冒了股烟,再也开不起来了。这之后,我常常跑到街上的网吧去上网,那个年代BBS(网络论坛)盛行,我在好多网站流窜,像左岸会馆、天涯、新小说论坛等等,在虚拟的世界里找到了一群朋友,于是也开始写小说。那时候,左岸上有一大批后来变成很活跃的作家,徐则臣、王棵、李浩他们是小说版的版主,我第一个像样点的小说就发表在网上,当时《小说选刊》的副主编还夸了我一顿,深受鼓舞,于是一坚持写了十多年。 问:童年生活对你的写作有深远影响吗?我注意到,你的短篇小说《告密》(《收获》2016年第3期)和《你好,妈妈》(《江南》2018年第2期)等作品,都涉及对童年生活的回望和反思。 答:我相信童年对每个写作的人都有影响,文学作品中的童年是具有启蒙精神的,它也最接近于文学表达,而我最早接触到的小说,比如《恶童日记》《杀死一只知更鸟》等等,对我后来的写作产生了一定影响。只是写到后来,得去考虑什么样的叙事是中国式的,对童年的回望和追述其实有对生命个体和历史纵深的反思,当下和过去,现实和历史,是一脉相承且彼此印证的。 问:《告密》从儿童视角看成人世界,尤其是特定阶段的政治、历史与文化,所蕴含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比如里面写到“我”跟父亲聊天时的隔阂。“我”觉得跟父辈聊天是很困难的,因为在聊到一个人的时候,大人们总会去追问这个人的父辈是谁,他们家原来的情形怎么样。那是一个重血统、重阶级出身的年代。书写这样的细节,跟你的个人记忆有关吗?还是主要是想对特定的历史时期进行反思? 答:这个小说源于我和父亲的一次聊天,聊到了一个家族的过去和现在,脾性和血统,我突然被过去的某段历史击中并深深地着迷。后来这个小说写出来后,就面目全非了,我是一个散漫被动、目标经常发生偏移的人,经常被一些有意思的,或者说更接近于文学本质的东西给带着走。这个小说写得很顺利,出奇的快,写完后,我就发给了走走,小说在他们那里看了一轮,这期间,我也反复在看,总觉得哪里好像出了点问题,后来他们给了意见,其中王继军的意见很中肯,他说结尾之前的几段视角出现了问题,不是一个小雷默在讲述,而是一个大雷默。我豁然开朗,后来儿童视角一直贯穿了整个文本,里面的人物都是虚构的,国光是我童年记忆的缩影,在他身上集合了我很多小伙伴的影子。儿童视角有一点什么好处,就是能触及历史的深处,而且简单和天真在很多时候是有效的,如果换成成人视角,不见得能很好地转换。 问:读《告密》,“我”和国光是两个给我印象深刻的人物。可以说国光曾经是一个坏孩子,比如他曾经当着“我”的面,跟别的同学放肆地大笑,以此来嘲弄“我”的孤立无援。这种“儿童世界的政治”,可能是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遇到的。我记得史铁生在他的散文和小说中都反复写到类似的经历。对于孩子而言,这是恐怖的记忆。但《告密》中“我”和国光从结怨到和解,这个结果才是我所期望看到的。我觉得你既试图写特定时期或人性中或隐或显的恶,但又不忽视细小的善,还有星火般的希望。这比一味地写人性的恶或写恐怖的记忆要强。 答:我现在时常在思考,文学作品中那些纯良美好的人物太少,可能不是写作者不愿意写,而是能力和情怀的问题,我们接触到的日常,大部分是无法让人愉悦的,塑造一个让人感动且具备信服力的人其实是很难的。自现代主义的小说出现以来,我们的这种传统正在流失,比如浪漫情怀,比如具备了飞扬气质的书写,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底层,苦难,和对现实无距离的紧贴,我们被训练得整齐划一,只会一个动作,这其实对文学审美的形态是一种破坏,健康的审美必须是多元的,就像一个森林,必须有乔木、有灌木,有草本植物。 问:《告密》《大樟树下烹鲤鱼》,还有《风景如画》《深蓝》等,都可以说是“以小见大”的作品——开口很小,往里走,却渐渐阔大,甚至有无法言喻的深厚意味。在《风景如画》中,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但是通过“我”试图隐瞒自己吸烟的事实,把“我”与母亲、与浩明等等的关系给写活了。《风景如画》是一篇略带黑色幽默的作品。“以小见大”是你在小说创作中有意追求达到的效果吗? 答:我已经听好几个人这么形容过我的小说,其实我没有刻意追求这种效果,小说的容量本来就应该超过故事要表达的范畴。我现在的工作就是编小说,在小说与故事之间,我常跟人说,小说如果是讲故事的,除了故事,还有什么是很重要的?文学作品的弹性和张力在哪里?这其实是衡量一个作品好坏的一方面,如果故事把小说包满了,就太实了,意味也就死了。我好多小说其实写之前有一个想法,具体怎么写是没有定数的,我喜欢走进小说人物的内心,遵循人物的内心往下走,那样的写作顺利起来还好,不顺利时会很折磨人,来来回回地反复折腾,其实也在折磨自己的内心。每个具备了一定能力的小说作者都希望能找到最贴切、最准确的可能性,所以,写小说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拷问自己的心灵。 问:我个人很喜欢《深蓝》这一篇,里面的王武同样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小说里写到他对“精神生活”的重视,比如在船上带着色情杂志,这对“精神生活”有轻微的反讽,小说后面还写到他偷偷地带了儿子的遗像上船,这又让他的“精神生活”有了庄重之意。先是反讽,继而庄重,既真实,又有很好的美学效果。王武竭尽全力地救失足落水的“我”,并最终意外身亡,这个场景的安排也很好,可以说是小说最有力量的部分。你为什么会想到写《深蓝》这篇小说? 答: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个小说,所以花了很长的时间用来修改,改完以后的小说和最初的那个版本肯定差别很大,总体更贴近于我的审美。这个小说看完以后,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只写了冰山一角,这正是我想表达的,剩下的都自己去猜吧。当时怎么想到写这个小说的,我忘了,记得有一回,看到一个远洋渔轮杀人案,挺恐怖的,当时也没觉得这是可以写小说的,当下笔的时候,它突然就自己跑出来了。我其实对那种深蓝的颜色很迷恋,这是一种忧郁的色彩,小说也想把这种气息营造出来。王武带着自己儿子的遗像出海,他当然知道犯忌,可还是出海了,这就是生活。他见不得人落水,除了那条抑郁的狗,当然也有别的原因,这里面我总觉得三言两语好像一时说不完。 问:你重视写作的风格化吗?如果重视的话,在小说写作上,你个人追求什么样的风格? 答:作家有自己的风格是好事,容易辨认,但你去看,最后都归结于小说语言,语言背后连接着作家对世界的思考和表达的方式,关乎个人学识、修养、视野、深度等等。其实现在很多写作的人风格是不明显的,但我相信他们都会有这方面追求。我个人倾向于简约且精准,师傅是卡佛,他同时也是很多人的师傅,当然,我也想把他更中国化一些。 问:你的小说《祖母复活》《大樟树下烹鲤鱼》正在改编为电影。受现代技术等因素的影响,今天我们正经历着文明历程的全球转向,按照尼尔·波兹曼的说法,这是从印刷文明转向视听文明,电影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表达方式。小说和电影,都可以说是以叙事为主体的,在电影变得如此重要的前提下,你觉得小说作为一种叙事的艺术,该如何彰显自己的特色?或者说,小说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答:写小说的人如果觉得小说没存在的必要,那为什么还写呢?小说是母体,依托小说,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如果一个电影没有原著,直接写成剧本,比如伊朗电影《一次别离》,你看完了,对它的评价还是:太好了,太像一个小说了!我个人觉得,两者的评判标准还是一致的,都可以调动人的感官,潜移默化浸润人的心灵。好的电影和好的小说都是向内的,都在可能性的问题上给出了独特的答案。电影是一幕幕的,需要几个生长的点,有的小说是不需要的,它完全可以是情绪的游走,小说可以在细腻程度上超越电影。说到底,两者都有自己的长短,可以并存。 问:如何看待你这一代人的写作?跟你们的前辈作家和后辈作家相比,你觉得你们的优势和不足有哪些? 答:我还真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的写作普遍不如余华、苏童这一代作家,不是放在同一个时空来比较,而是他们在20多岁、30多岁的时候,写出了哪些作品,他们的作品过去了那么多年,现在拿出来看还是熠熠生辉。我总觉得那个时代最精英的一群人都去做了作家,而到我们这一代,这个社会最精英的人去做了别的职业。毫无疑问,我们所处的时代选择太多,有很多人本来可能会成为很好的作家,但命运安排他们去干了别的事。总体来说,70后、80后这一代作家还是挺努力的,他们也大多处于上升的通道中,至于能写出什么样的成果,需要看造化。 问:接下来有哪些写作计划? 答:近期完成了一个长篇,是海洋题材,写了很多年,今年上半年狠狠心,完成了初稿,接下去准备修改一下,可能明年会发表或者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