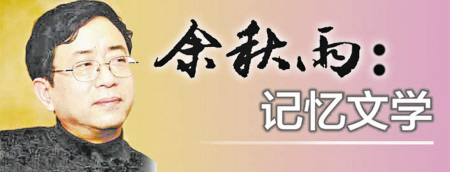 |
| 82 |
我不知道,我的长辈,当你们听说自己的一个孙儿成了“中国历来受诽谤最多的独立知识分子”时,会是什么感觉。是担忧、心疼、愤怒,还是自豪?这个称号,是几个学者经过认真调查才得出的。我当时一听也怀疑,后来仔细一想,如果不是只算一时一地,而是算二十年的连续不断,算每一次的全国规模,确实没有人能超过。 我估计,你们之中,独独对这件事感到自豪的一定是祖母,我已经看到她炯炯的目光。其他长辈,多少都有点困惑:怎么会是这样? 对此,我愿意接受你们的盘问。 代表长辈盘问我的,应该是离世最晚的您,余鸿文先生。 我似乎已经听到您的声音。您说:“讨论诽谤,不必看内容,因为那必定是假的。讨论诽谤,只看它为什么发生。”我点头。 于是您开始问了:“你和诽谤者之间,有没有权位之争?”我回答道:“自从二十年前辞职后,我没有任何官职,也不是什么代表、委员,又早就退出一切官方协会,因此没有丝毫权位可言,他们能争什么?”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利益之争?”我回答道:“我几百万言的研究著作,十几万公里的考察计划,从开始到完成,从未申请过一分钱的政府资助。他们能争什么?” 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学术之争?”我回答:“我的研究课题从来不与别人相撞,我的考察路线从来不与别人交错,我的表述方式从来不与别人近似。他们能争什么?”您继续问:“你与他们,有没有意气之争?”我回答:“你们看见了,那么多人连续伤害我十几年,有几个人已经把伤害我当作一项稳定的谋生职业,我却从来没有回击一句,也从来没有点过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我看到,祖母在您身后擦泪。 您停止提问,静静地看着我。 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了您的声音:“你的每一项回答,大家都可以见证。看来你是一个最不应该受到诽谤的人,却受到了最多的诽谤。造成这种颠倒一定有一个特殊原因,例如,刚才我想,是不是你太招人嫉妒?”我回答道:“嫉妒太普通,不是特殊原因。中国文化界可以被嫉妒的人很多,但他们都没有招来那么长时间的诽谤。”您说:“听口气,你自己好像已经有答案了。”我说:“我自己也曾经百思不解,后来,一番回忆使我找到了钥匙。”“什么回忆?”您问。 我说:“回忆起了我还没有辞职的二十多年前。那时候,我招人嫉妒的理由比后来多得多。我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最年轻的高校校长、最年轻的厅级官员,而且还执掌上海市那么多人的职称评选。我当时的行事风格,更是雷厉风行、敢做敢为。但是,整整六年,我不仅没有受到丝毫诽谤,而且也没有听到过一句非议。连后来诽谤我最起劲的那几个人,当时也全部对我甜言蜜语、赞颂不止。” “我已经猜到了你的答案了,”您说,“你遭到长期诽谤的最重要原因,是比较彻底地离开了一种体制。”我说:“体制是一种力学结构,就像一个城堡。身在其中,即使互相嫉妒,却也互相牵制,获得平衡和安全。不知哪一天,有一个人悄悄地打开城门出去了,城门在他身后关闭,而他骑在马背上的种种行为又经常出现在城里人的视线之内。他的自由,他的独立,他的醒目,无意之中都变成了对城内生态的嘲谑。结果可想而知,他必然成为射箭的目标。由于城门已关,射箭者没有后顾之忧。” “这样的城堡,可能不止一个吧?”您问。 “当然。”我说,“城堡的本性是对峙,如果只是一个,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现在,有的城堡因为有国力支撑而十分堂皇,有的城堡则因为有国外背景而相当热闹。我呢,只能吟诵鲁迅的诗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但是我比鲁迅更彻底,连戟也没有。” 您点了点头,似乎不想再问,却还是轻声问了出来:“堡外生活既孤独又艰险,你能不能,从哪个边门重返一个安全的城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