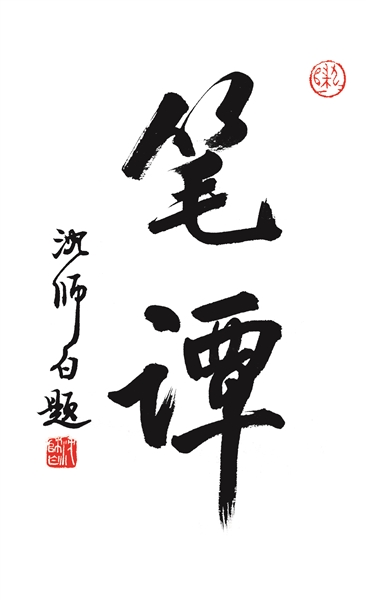 |
| 刊头书法:沈师白 |
暮秋初冬时节,总会想起母亲,因为我妈生日在1916年11月,忌日在2016年11月。忆母亲与忆童年是分不开的,童年时看到母亲是什么样子,在梦里就一直是那个样子——个子比我祖母高半头,身体壮实匀称,及肩的披发拢在身后,耳环闪着丝丝光亮。衣裳高高的领头里有两粒盘香纽,紧紧扣着脖子。我妈说话声音较粗,走路八字步,勇往直前的样子。 记忆里,我妈总是坐在自己房中静静地看书、写字。听祖母说,妈妈5岁开始读书,一直读到21岁出嫁。她的这一习惯,不曾因有了我和弟弟而中止。有时我轻轻走进去坐在地板上玩,她一点儿也不晓得,我慢慢走出房去,故意跳一跳,妈才惊起,大喝:“小居(宁波话,意为小鬼),你来捣乱是吧,当心我挈你到后山喂老虎去。”挈,是指她单手将我悬空拎起。那时我才六七岁吧,妈自然能轻易地将我挈着走。 有一回我问:妈!您这书要到什么时候才读完呀?回答:“古人云,书到今生读已迟,我今生这样读,来生还要继续读,听得懂吗?” 一门里厢,共住着我们4户人家,每家都是三代人,很热闹。前院是阿婆家和我家,后院五间两弄楼房,中间有祖堂,两边住嫂嫂婶婶家。祖堂是做红白事的场所,吓得我不敢去往后院玩。我妈说:你个小人,知道什么呢?有怕没怕!只要乖乖的,多读书,多干活,什么都不用怕。 我妈这样说,她自是不怕有鬼怪。上世纪70年代末,母亲年逾六旬。已常住上海的她忽然返乡住进故居自己的房间,怎奈此时门里厢已空空如也,老一辈都过世了,中年人住新屋去了,年轻人奔走四方。百年老屋几成危房。但我妈化不开乡愁,非要住一段时间不可。在她心目中,这里依然还是当年十里红妆做新娘时的花烛洞房。不久妈写信告诉我,每到深夜,前后两排空屋就会发出奇异的声响,干扰睡眠。某夜,声响又起,我妈想反正睡不着,不妨看看究竟是啥东西在发声。于是更衣推开门,院子里月光如水,响声却戛然而止。她踏遍前院后屋,不见有何异物,她对空问话,四周并无回声。当回房睡下,声音又起。看来是拗不过自然,住些天后,妈又重返上海了。 夏夜院子里乘凉,只要有月亮,我妈就会讲故事。门里厢阿婆、大妈、嫂嫂、姐姐,都已听惯了。大家自带椅子,静静地听:唐明皇游月宫、广陵散、伯牙摔琴谢知音等等,每晚讲一段。这些故事大多是妈从古书上看来的,好在她释成了大白话,我和小伙伴们都能听懂。有时也讲古代笑话,一院子人笑得前仰后合。 我们海边的村村岙岙,人丁兴旺,不少农民读过几年私塾,村里一般的抄抄写写可自理,偶碰到有难懂的字或古文,就来问我母亲。我妈总是先请他们到后院祖堂八仙桌旁稍坐,远村来的则先请用茶,自己穿戴整齐,带上文具匣,才去详细讲解。平时也有乡亲来请母亲写这写那,如墓碑大字,红白诸事的祝文、悼词,古诗词条屏、楹联等。不知从何时起,村人给我妈起了个号:康熙字典。在背地里叫了一个时期,觉得不太敬重,就改称杨先生。我妈听到这个称呼,赶紧制止:我名杨贺孺,直呼名可以,但不可叫我杨先生,这是人家称呼我父亲的,先父(杨霁园)虽已不在人世,但先生之名万古千秋。听了这个解释,大家终于想出了一个恰当的叫法:贺先生。1950年村里办起农民夜校,请我妈任教,于是又改称“贺老师”。 我妈是个快乐风趣的人。她喜欢给人家起绰号,她取绰号往往即景应人,随口喊出,通不通俗无妨,释放那种意思就是。她叫自己“隔山飞”,叫我“小居”,还有暗里头叫人家单括、妈姆、七雕开园、阿巴公、此牙悦者、门客等,先把自己逗乐,又让大伙儿开心大笑。她的欢乐多自心而出,能感染别人。 1953年3月,在上海工作的我爸拿来证明,让我妈迁户口去上海定居。这一去就长住了,其间只来过老家几次,先后送我的三个弟弟去参军。有人对我妈说:太大意了,听说外面在打仗呢。我妈平静地说:“有段戏文唱词,‘我儿既有报国志,为娘岂无热心肠。秋去冬来天已冷,劝儿多带夹衣裳。’哪个战士不是父母生、父母养的啊。” 在我爸87岁、我妈88岁那年,两位寿星叶落归根,卖掉沪上住宅,返回故乡鄞州瞻岐卢家村,新购独院小楼一套,取名养老斋,过起了“红袖添香对译书”的安闲日子。常有村人来讨要两位老人的字画,说二老福禄寿齐全,手迹挂在家里可带来吉祥。此时,我的三个弟弟都已转业,大弟落户杭城,小弟居甬城,唯二弟执意回故土侍奉高堂双亲,并在溪泉之畔新造楼房四栋。我定居宁波主城区已多年,起初一年里总有好几趟看望父母,但上了75岁,坐长途车会呕吐引发高血压,无法成行。只能打电话请安了。 我妈说,有时铃声响没听到,能否约定一个通话时间?最后商定,每日下午4时半,我打电话过去。我妈特高兴,电话里笑哈哈地说:“小居,别忘记,下午4点半!噢,我家院子里夕照温暖,我听好电话就可以吃晚饭了。” 致电问安在黄昏之前,持续未到3年,母亲因脚痛,住院3日,就与世长辞,享年101岁。我父亲因消化道疾患,先于2010年逝世,享年94岁。风景独好的养老斋人去楼空。满院花木,在寒风中犹放阵阵清香。
|